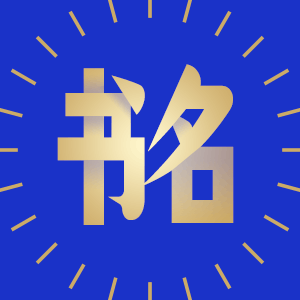野蛮生长后中国网络文学已成世界奇观
目前中国网络文学用户已达3亿。经过近20年的迅猛发展,网络文学不但形成了自成一统的生产—分享—评论机制,也形成了有别于“五四”“新文学”精英传统的网络大众文学传统,这一切都对传统学院批评体系构成挑战。
传统文学对“网络性”毫无感知能力
陈晓明:对网络文学我们今天有很多争论,有很多人还在争论它是不是文学?它是不是好的文学?我觉得这种讨论现在必须pass,因为它永远纠缠不清楚。我想到一个文明的问题,网络文学可能真是文明的变化所带来的变化。我也认为今天是视听文明的时代,可能还可以升高一个层次来理解它,这是一个虚拟文明即将到来的时代。所以想请两位谈一谈从虚拟意义上,网络文学意味着什么?
李敬泽:邵老师所提出的问题是针对印刷文明向电子文明的转化过程,是向着文学或者向着人类书写形态转化提出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中就包含着一些新概念。你好像用过一个词是“网络性”,这个“网络性”就是很有意思的东西。它不一定指的仅仅是网络,可能是伴随网络时代而来的一切东西,包括刚才谈到的虚拟现实,游戏等等。我觉得网络性是更重要的东西,也就是说,也许有的网络文学是没什么网络性的,也许有些所谓的传统文学反而是有网络性的。这个网络性又是如何界定的呢?
作为“守墓人”,我一直是满怀着一种危机感。如果对照一下文学史的进程,你就会觉得很有意味。比如欧洲文学,你看它在二十世纪初现代文学开始产生时的模样。我记得在伍尔夫的书信里,她非常严肃、非常深入地探讨什么问题呢?探讨电报意味着什么,探讨火车意味着什么。他们谈到速度问题,整个人类的生活速度的变化,他们当时也是充满了激动,思考当媒介速度发生变化的时候,这变化对人意味着什么?对生活意味着什么,对文学又意味着什么?所以,欧洲人的现代主义不是凭空来的,不是在屋子里憋出来的,是面对整个生活形态变化——电报发明,火车发明,枪炮的进化和大规模现代战争的出现,同时还有弗洛伊德等等——而做出的反应。伍尔夫说在新的条件下,人的概念要重新定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对文学重新定义。
进入网络时代,我们面临着“网络性”的考验。但是现在,传统文学对“网络性”是缺乏感知能力的。至少在这几年的小说里,我也没有看到有小说家,包括年轻小说家,在认真思考我们现在的生活形态,对于人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于文学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没有能力从这样一个新的条件下,对人提出新问题,对文学做出新的界定,开展对新的可能性的探索,我觉得是大问题。
反过来看网络文学,实际上你深入进来看,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其中包含着旧东西的复活,但旧东西不一定是坏东西,旧东西也许就像我们谈类型文学一样,它是人性中非常恒常的东西,是千锤百炼,你永远都得走这个套路的东西。关于言情小说怎么写,说老实话,从明代到现在,没有太大的变化。比如,昨天晚上我还溜了几眼的电视剧《翻译官》,固然加入种种新的元素,但你看两集就看出来了,根本套路没有太大变化,基本上就是琼瑶剧在网络时代的升级版。当然《翻译官》很好看,它一定是好看的。一方面是旧的东西又回来了,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网络文学中确实有大量的,叫做“网络性”的因素或者元素。我甚至不能说网络文学一定是属于有“网络性”的文学,相反,传统文学里有的倒是很有“网络性”。
文化输出
网络文学走到了前面
邵燕君:以中国网络文学为例来研究网络文学,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网络革命在全世界发生,为什么网络文学在中国风景这边独好?中国是一个特例,但这个特例并非特异,它跟中国特有的文化制度直接相关。
国外没有像我们这样有如此成规模的网络文学,但这并不代表它们不需要网络文学。“女频文”在东南亚地区一直传播很广。近年来,美国出现了一批粉丝自发组织的以翻译和分享中国网络小说为主的网站和社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2014年创建的WuxiaWorld(武侠世界)。它以翻译仙侠和玄幻等网络小说为主,第一部被翻译的小说就是“我吃西红柿”的《盘龙》(《COILING
DRAGON》)。建站不到两年,WuxiaWorld已经发展成为北美Alexa排名前1500名的大型网站,目前日均来访人数已稳定在50万以上。目前看到的只有英语翻译,来访人数排名前几位的国家分别是美国、菲律宾、加拿大、印尼、英国,一共80几个国家,其中来自美国的访问量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
WuxiaWorld等美国的中国网络小说网站和社区不仅已经有相当规模,更重要的是,这完全是这些“老外”粉丝们的自发行为,运营方式是,网站招志愿者翻译,每人负责翻译一部小说,通常每周会保底翻译更新三到五章,此外也接受粉丝的捐赠,一般每捐赠满80美元或60美元,志愿者就会再加更一章。在漫长的追更与日常的陪伴中,中国的网络小说真正显示出了它的文化魅力,成为了中国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李敬泽:也就是你论证在网络时代我们终于走在了世界前列?
邵燕君:只是网络文学走在了前列,现在讲文化输出,如果说美国有好莱坞,日本有动漫,韩国有电视剧,中国就是网络文学。前几年风靡全球的美国的《五十度灰》,在中国就是火不起来,因为放在我们的女频文里,这是很一般的“霸道总裁文”。韩剧《来自星星的你》,那种“梗”在网文里也是几年前流行的老套。但我们的产业链不配套,动漫、影视和游戏都落在后面。现在从网文到影视剧播映的时间差大致是5—10年,比如《琅琊榜》《甄嬛传》都是十年前的“老文儿”了。
回过来说,为什么中国网络文学风景独好?这与我们新中国以来特殊的文化出版体制直接相关。简单地说,我们在印刷文明时代,商业类型小说不发达,没有建立起那一整套生产机制,没有培养起一支创作力旺盛的类型小说作家队伍,更没有形成一个充分细分、精准定位的市场渠道。整个1980年代文学都是精英化的,1990年代“市场化”转型之后,类型小说基本都是外来的,金庸、琼瑶、斯蒂芬·金等。这时有出版界人士开始建立畅销书机制,如安波舜的“布老虎”丛书,后来兴安也提出“类型小说”的概念,但还是有多重限制。这时,网络进来了。网络文学吞下了印刷文学没有吃到的最大一块商业蛋糕——类型小说,而且当时网络空间也确实没人管,再加上先进媒介蕴藏的巨大能量,经过十几年的野蛮生长,就长成了现在这样的世界奇观。其实在网络时代,文字的艺术已经不是“最受宠的艺术”,是印刷文明的“遗腹子”,如陈老师刚才所说,网络时代是视听文明的时代。但正是因为文化体制的特殊原因,让这个“遗腹子”阴差阳错地获得了一个得天独厚的发展机会,也使中国的网络文学获得了一个“弯道超车”的契机。
李敬泽:当你谈论这个契机的时候,你实际上已经谈得不完全是网络文学,你谈的还是通俗文学的“补课式反弹”。
邵燕君:但如果没有媒介革命这个契机,这种“补课式反弹”很难发生,更不会形成文化输出的态势。像欧美日韩这种文化商业机制充分发达的地方,靠那些超市买的畅销书,读者已经吃得很饱了,读者俱乐部等社群也很成熟——不过,看他们今天字幕组翻译的情况,恐怕也没有吃得那么饱,或者,我们用网络媒介炒出的菜更有诱人之处——但不管怎么说,纸书读者会有很强的“路径依赖”,而且,纸书也可以很好地保护作者版权。这时,网络媒介出来,就会被用来发展ACG文化,或进行跟网络媒介更相关的文学试验(编者注:ACG是英文Animation、Comic、Game的缩写,是动画、漫画、游戏的总称)。中国网络媒介刚刚出现的时候,网络文学是五花八门的,现在也是五花八门,只是我们看不见太小众、太具先锋试验性的创作了。因为类型小说的产业规模太庞大了,以至于我们现在谈网络文学就是指网络类型小说,而且这么说也确实更明确,更干脆。
这就谈到了中国网络文学奇观发展的另一个原因,也是另一个占便宜的地方。本来在网络时代,ACG文化是来和文学分读者的,目前在中国也是这样,但在最初的时候不是。中国网络文学兴起之前,通过各种正版盗版渠道,中国已经积累了大量的ACG文化粉丝。网络空间一打开,各种“二次元”文化的粉丝一股脑栽进了网络文学领域,成为最铁杆的粉丝和最具创造力的生力军。我在课上问同学们为什么写同人小说?有的同学给我的回答居然是“因为我不会画画儿”。他们说,老师您不是印刷文明的遗腹子,我们才是!因为他们看动漫长大,但是不会画画,只能用文字写小说。所以,ACG文化的反哺也是中国网络文学得以高速发展的得天独厚之处。
一个古典时代的读者,完全不能理解现代粉丝是怎么回事
陈晓明:我们困惑网络文学何以有那么大的能量?这种互动机制是怎么产生的?我特别想听两位探讨一下,在整个网络文学生成中,人的主体发生了什么变化?起了什么作用?这才是根本的。
李敬泽:前些日子凡客的老总陈年被骂得狗血喷头,他无限地崇拜穆旦,别人问他周杰伦怎么样,他一听急了,周杰伦怎么能和穆旦相提并论呢?对于穆旦来说,周杰伦就是垃圾。结果陈年现在是一身的垃圾了,已经被骂得一塌糊涂了。我觉得这就是你所说的一个古典时代的读者,完全不能理解现代的粉丝是怎么回事。某种程度上讲,周杰伦确实和穆旦不一样。穆旦是一个封闭起来的作者,一个自我创作的作者。而周杰伦在他的整个演艺过程中有无数粉丝的参与,因此,很多人都觉得,你说周杰伦是垃圾,让我的情感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和伤害。伤害广大人民群众的感情,这个事是很大的。确实在这些方面有一些重要的事情正在发生和已经发生,而且这些重要的事情,确实需要一种文明经历一个较长时段才能看得清楚。
邵老师谈到印刷文明时代作者是孤独的。其实不仅是印刷文明时代,起码在中国司马迁以后就有了孤独的作者了,他在那儿一个人发奋,说“我要不朽”!这种“不巧”的意识基本上是从汉代确立起来的。但是,网络写作的情况其实变了。现在网络文学依然有一个可辨认的,放在那儿活生生的作者。但是网络文学的读者和作者之间,也就是所谓粉丝和作者之间,他们的阅读关系、情感关系,包括在创作上的参与关系,确实已经和过去的传统关系完全不同了。这个变化能从根本上动摇传统文学从创作到阅读到传播的整个链条。
邵燕君:为什么网络文学调动起读者这么大的热情?就是因为与每一个读者那么的直接相关,粉丝具有很强的“参与性”。网络文学是依靠粉丝经济的。这个粉丝经济不是只有钱,还有爱。好的粉丝经济机制,能够把“有钱”和“有爱”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比如我订阅,我打赏,并不仅仅是把钱拍给你,这本身是表达爱的方式。这个我有体会。我刚开始也不能接受“打赏”这个词,直到有一天我追文的时候,看到一段特别感动,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我就说“赏”!这时候,说什么都是虚的,一百块钱打下去最实在。给钱不一定“有爱”,但不给钱,真是很难说“有爱”。
刚才敬泽老师谈到的“参与性”创作,是粉丝文化之中最高等级的那部分。一般的读者即使不参与创作,也在漫长的追更中,与作者、与其他读者形成一个“情感共同体”。对于网络文学读者来说,“追更”本身是一种生活,一段时光。比如《海贼王》一说要完结,大家就说这么多年我就是靠它“拌饭”的啊!传统文学这边评论起网络小说,经常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动辄几百万字”,言下之意是,这么长,一定是垃圾!这么说时有没有想过,我们的一些美学原则,比如惜墨如金、言简意赅,可能与纸张的匮乏有关系。纸书最多也就100万字,但是,要和古人的尺牍相比,也是很长啊!
类型文是国民心态的风向仪
邵燕君:网络文学发展十几年来,出现了大量的类型文,有些是舶来的,但极度发扬光大,如穿越、耽美;有些是本土原创的,如盗墓、宫斗、种田。每一个新类型的出现,每一种类型变形,都对应着一种社会思潮的出现和变化。如果我们说社会思潮像汹涌澎湃的洪水,类型就是洪水过后留下的河道。我们专业性的文学研究一定要把内容落实到形式,不但要看写什么,还要看怎么写,要把社会思潮的变迁落实到类型文模式的变化上。
比如,穿越小说中的“清穿”(穿越到清朝)直接继承的是琼瑶小说的言情模式。2004年的开山之作金子的《梦回大清》里,还是“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一年之后的《步步惊心》,已经是生存压倒爱情:若曦深深爱着八爷,但因为知道历史的结局,强迫自己转向了最后的胜利者四爷,对于她的趋利避害,读者也是在无奈中认同的;到了2006年的《甄嬛传》,“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已经是痴人说梦,于是,“清穿文”变为“宫斗文”、“宅斗文”;再往后,又变成了“种田文”,女主人公根本不谈爱情,一心一意地过好小日子。从“清穿”到“种田”,言情模式走向了反言情,但实际上缓解的仍然是爱情的焦虑。2015年,网文圈又盛行“甜宠风”,人为设定“一生一世一双人”,没有小三,没有宅斗,两个人不吵架,不作死,甜甜蜜蜜地互宠,手拉着手去打天下……而如此乐观的设定,对应的恰恰是在现实生活中,女性的安全感越来越受到威胁。姑娘们只好创造一个虚拟的世界,自己甜宠自己,自己“富养”自己,让自己长成更健康的人格,更好地面对现实。所以,很多人认为网络文学脱离现实是不对的。这里,所有的幻想都是现实焦虑的折射,更文的形式使这种折射特别及时,类型文的变迁正是社会价值和心理趋向变化的轨迹。
网络文学拓展了我们这个时代中国人对自我的想象
李敬泽:如果回到布鲁姆《西方正典》的意义上,所谓经典,应该是在一种文化和传统里,那些对一个人的自我认识起了非常非常重要作用的作品。在这个意义上说,应该说网络文学开辟了新的很重要的路径,拓展了我们这个时代中国人对自我的想象。某种程度上讲,这个也是我们的传统文学所匮乏的。因为我们现在传统文学,说老实话,已经是严重受制于经典背景,并且是西方文学的传统背景。沿着这个传统下来,你就会发现,我们传统文学对人的形象的想象,基本上是破坏性的,或者是一个否定性的想象方向。
关于网络时代的人可能成为什么样子?在这方面反而是我们的网络文学有些开拓,这里面有些类型还真是蛮有意思的。我不能肯定哪一部作品一定是经典,但是我想它们确实是开拓了一些新的空间,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