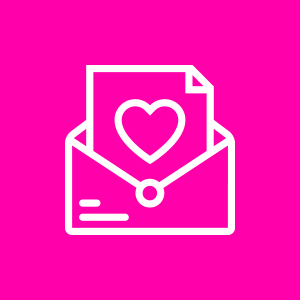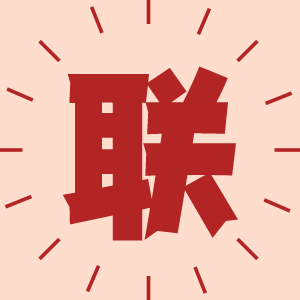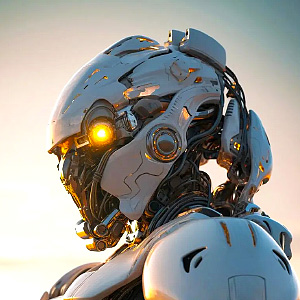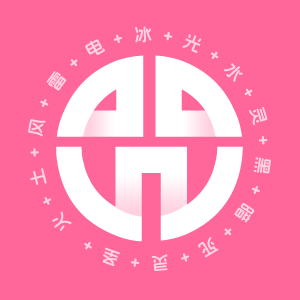人文通史 古代妓女的种类与名目
妓女,是性侮辱和性玩弄的典型表现,也是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中女子低贱地位的具体表现。这种现象,到了秦、汉与魏晋南北朝,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一、营妓
在这个时期,妓女的一个很大发展是出现了营妓。营妓始于汉,历六朝、唐、宋而不衰。“一曰,古未有妓,至汉武始置营妓,以待军士之无妻室者”。其实,如上一章所说,妓女在秦汉以前已经出现,而且勾践采取过“游军士”、管仲采取过“女闾”的做法,不过到了汉武帝的时候,把设营妓作为一项制度定下来而已。汉武帝是个具有雄才大略、好大喜功的皇帝,他对外连年征讨,用兵很多,所以如何稳定军心、提高士气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设营妓就是这方面的措施之一。其他还有许多对军人优待的措施,如《汉书·冯康传》说:“赵将李牧为边将,居边军市之租,皆自用飨,赏赐决于外。汉魏尚为云中守,军市租尽以给士卒,出私养钱,五日一杀牛,以飨宾客军史舍人”等等。
在汉朝未正式地设立营妓以前,有一种妇女“抑配”军营的制度,所谓“抑配”,就是强制地许配。汉朝的大将李陵率领军队出关东,把一些强盗的妻子押送到军中随军“抑配”给一些士兵当老婆,这些女人不愿意,躲在车中不肯出来,李陵把她们搜查出来后,用剑把她们都斩了。当然,这种“抑配”制在当时并不普遍,而且有不少缺点,士兵甚众,而随军妇女不可能很多,否则将使军队臃肿,行动不便;而有人有妻有人无妻又易造成矛盾,所以后来从统治者看来,还是设置营妓,让士兵们共同享用、平均发泄性欲为好。妓女也要作一些“服务”。
关于营妓,在以后的历史上也多有记载,如夏侯淳征孙权有功,曹操曾赐给他“妓乐名娼”,于军中享用。北魏元琛任秦州刺史时,“诸羌外叛,屡讨之不降,琛令朝云假为贫妪,吹篪而乞,诸羌闻之,悉皆流涕,迭相谓曰:何为弃坟井在山谷为寇也?即相率而降。秦民语曰:快马健儿不如老妪吹篪”。朝云就是当时元琛征讨诸羌时的随军妓女,看来营妓除供士兵发泄性欲以外,有时还有配合军事行动的作用。又如,南朝萧梁时章昭达奉命出征途中,“每饮食,必盛女伎杂乐,备羌胡之声,音律姿容,并一时之妙,虽临敌而弗之废也”。宋后废帝每出入去来,尝自称刘统,或自称李将军,与右卫翌辇营女子私通,每从之游,持数千钱供酒食之费。齐废帝尝与左右无赖群小20余人共衣食,同卧起。帝独住西州,每夜辄开后堂,与诸不逞小人,至营署中淫宴。这都无疑是沿袭汉代的营妓制度。
二、家妓
家妓就是畜养在家庭中的妓女,而不是在坊曲或军中的。畜养家妓的风气始于汉代,而极盛于南北朝。这种情况,历史上记载很多,例如晋朝的谢安在东山畜妓,每出游,必以女妓从。《晋书·陶侃传》:“媵妾数十,家僮千余,奇巧宝货,富于天府。”《魏书·高阳王雍传》:“又与元义同决庶政,岁禄万余,粟至四万。妓侍盈房,诸子端冕,荣贵之盛,昆弟莫及。……后多幸妓,侍近百许人。”以上情况,都说明了这个时期家妓之盛。在这些官僚、地主、富豪家庭中的家妓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她们只是主人的一种娱乐和发泄性欲的工具,没有任何人身自由,主人对她们有生杀予夺之权。
如曹魏时的曹璋看中了别人的一起名为白鹘的马,就说“予有美妾可换”,结果实行了交换。《玉台新咏》中《和人以妾换马》一诗中所说的其实指家妓。曹操有一名家妓,色艺超群,尤其是她的歌喉最好,无人能及,但是,这个女人性格不好。曹操讨厌她,想杀她,可是又舍不得她的歌喉,于是就选美女百人一起训练,其中有一个女子进步到可与那家妓相媲美的程度,曹操就把这个家妓杀了。又如西晋王恺有一次请王敦等人来家中做客,命家妓吹笛,有个吹笛妓女略有小忘,王恺就叫人把她活活打死了。
第二,这些家妓与妾略有不同。
家妓对主人多以歌舞乐曲提供艺术与娱乐服务,所以必须对她们施加这方面的训练,当然,她们也要提供性服务,这就要看主人的喜欢与需要了。正因为如此,晋朝的殷仲文劝宋武畜妓,宋武说:“我不解声。”这就是说,我不懂音乐(可能也不喜欢音乐),畜家妓有什么必要呢?而妾,则不一定需要经受什么训练,也不必有什么艺术才能,只需陪主人睡觉,供他发泄性欲而已。同时,还可以看到,家妓的地位比妾略低。后魏有个叫高聪的人,畜家妓十多人,不管她们是否为他生过子女,一概注籍为妾,以悦其情,笼络人心。可见,家妓的地位似介于妾与妻之间。应该指出,家妓在史以及中国古代艺术史上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她们往往是所处时代歌舞艺术的代表,她们为了符合当时统治阶级的需要,绝大多数受过严格的艺术训练,具有良好的文化教养。以石崇训练翔凤等妓女为例:“石季伦爱妾名翔凤,魏末于胡中得之,年始十岁,使房内养之。至十五,无有比其容貌,特以姿态见美。妙别玉声,巧观金色。……崇常择美姿容相类者十人,装饰衣服大小一等,使忽视不相分别,常侍于侧。使翔凤调玉以付工人,为倒龙之珮,萦金为凤冠之钗,言刻玉为倒龙之势,铸金钗象凤凰之冠,结袖绕楹而舞,谓之‘恒舞’。欲有所召,不呼姓名,悉听珮声,视钗色,玉声轻者居前,金色艳者居后,以为行次而进也。使数十人各含异香,行而语笑,则口气从风而飏。又屑沉水之香,如尘末,布象床上,使所爱者践之,无迹者赐以真珠百琲,有迹者节其饮食,令身轻弱。故闺中相戏曰:‘尔非细骨轻躯,那得百琲珍珠。’”从以上可见,翔凤等家妓从十几岁起就在石崇的亲自指导下学习歌舞,既接受严格的基本功训练,又进行身材、舞姿的修炼。石崇是通过重奖的刺激来促进与实现这些的。因此,这些家妓的歌舞艺术(当然还有其它艺术如杂技等)大致可以代表当时这方面的艺术水平。西汉傅毅的《舞赋》详细地描写了当时的大型歌舞水平;而张衡的《二京赋》又具体地描写了当时“角抵百戏”(即杂技)表演的盛况。
在这些家妓中,有不少人乐器演奏也很出色,例如魏王饮宴时既有“楚姬舞于前,吴姝歌于后”,也有“越女鼓瑟于左,秦娥泛筝于右。”汉武帝时的张骞从西域引进“胡乐”以后,出现了一些擅长演奏某种乐器的家妓,如箜篌妓、琵琶妓、鼓吹妓等,例如东汉的刘康家中就有一名“鼓吹妓女宋闰”,当时相当出名。有的女妓还多才多艺,乐器、歌舞全面发展,例如北魏女妓徐月华,“善弹箜篌,能为《明妃出塞》之歌”,她有一次“徐鼓箜篌而歌,哀声入云,行路听者,俄而成市”。《玉台新咏》中有不少描述妓女的诗,反映了这方面的状况。
第三,家妓的物质生活远比一般平民优厚。
这是因为,她们既是主人的一种娱乐和发泄性欲的工具,那么主人对她们也要像维修保养工具那样对待,像喂狗以肉、喂猫以鱼那样对待,以达到自己享用的目的。这些官僚、地主、富豪不仅以畜妓弃之多以炫耀其权势与财富,同时,也把这些家妓蓄意打扮,锦衣美食,以夸耀其地位与奢侈豪华。例如《南史· 徐君倩传》:“为湘东王镇西谘议参军,颇好声色,侍妾数十,皆佩金翠,曳罗绮,服玩悉以金银。”《宋书·恩倖传》说,阮佃夫“权亚于人主,宅舍园地,诸王邸第莫及。妓女数十,金玉锦绣之饰,宫掖不及也。每制一衣,造一物,京邑莫不法效。”西晋石崇畜成百上千名家妓,“皆蕴兰麝,被罗縠”、“曳其绣,珥金翠,丝竹尽当时之选,庖膳穷水陆之珍”。北魏元雍“妓女五百,隋珠照日,罗衣从风”。元琛还专为妓女”造迎风馆于后园。窗户之上,列钱青锁,玉凤衔铃,金龙吐珮,素柰朱李枝条入檐,妓女楼上坐而摘食”。看来,这些家妓是作为一种高级装饰品、奢侈品而流通于男人世界,任其男人支配和使用的,不论她们的物质生活是多么优厚,她们只不过是男人的祭品而已。
三、官奴隶
这个时代的宫妓和家妓都和奴隶制度有密切关系,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没有人身自由,不得已而为之的。这个时期的奴隶来源,一是俘虏。当时,战祸频仍,首先是连年征讨,以后是三国之战,五胡十六国袭扰黄河流域,为我国历史上种族大变动、大转移时期,胜则为王,败则为寇、为俘虏,一些被征服了的民户也被徒为“杂户”、“营户”,并世代相袭,即使换了朝代,仍然要做奴隶,其妻儿老小,概无出头之日。北齐后主武平七年三月,即公元563年,括杂户女年二十以下十四以上未嫁者,悉集省,隐匿者家长处死刑。这此杂户和营户的女儿可以任意被集中起来,作为各种形式的妓女,供男子蹂躏。二是罪犯家属。前面所述的“抑配”制度与此就有密切关系。又如《魏书·刑法志》说:孝昌以前(按即公元525年以前)天下淆乱,法令不恒,或宽或猛。及尔朱擅权,轻重肆意,在官者多以深酷为能。至迁邺,京畿群盗频起,有司奏立严刑:凡强盗杀人者首从皆斩,妻子及同籍配为‘乐户’;其不杀人、赃不满五匹,魁首斩,从者死,妻子亦为‘乐户’;小盗赃十匹以上,魁首死,妻子配驿,从者流。
《魏书》所谓“乐户”,即指女乐、倡优等歌舞艺人的户籍,乐户与营户、杂户一样,被认为身份低贱,不属于良民,乐户中的女子就是妓女。凡乐户“皆用赤纸,其卷以铅为轴”。由于是盗贼的家属而受株连,终其身沉沦于女乐、娼妓之途,而且世世代代几无出头之日,这实在是非常悲惨的。这种状况,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都是实行的。如晋朝的范坚犯了死罪,他的女儿乞恩辞求,自愿没为奚官奴,以赎父命。宋女巫严天为劫坐没入奚官。这里的“奚官”就是为娼。《隋书·刑法志》上也说:“梁制:大逆者,母妻姊妹及从坐者,妻子妾女,同补奚官为奴婢。其劫盗者,妻子补兵。”又说:“魏、晋相承,死罪重者妻子皆以补兵。”所谓“补兵”也就是补入营妓的行列。
四、私妓
所谓私妓,是指在城市妓院中出卖肉体的妇女。她们不同于家妓,不是专门属于某个官僚、地主或富豪所有,不是对个别或极少数人出卖肉体,不是专门为军队服务,而是面向社会的一切男子。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主要不是以高超的歌舞技艺来博取男子的欢心,她们没有这样的训练条件,而且一般男子也付不起这么高的价钱,她们的存在主要就是为了解决社会上众多的男子性饥饿的问题。由于战争频仍,也由于生产的发展,人口流动大大增加,一些将士、手工业者、商人、市民以及一些散兵游勇,都是她们的顾客。当然,私妓是有不同层次的,由于社会各阶层人士的需要不同,私妓也有高、中、低的区别,高级妓女往往是有色有艺,文化素养很高,才思敏捷,甚至为家妓中的佼佼者所不及。她们并不随便向嫖客献身,而往往和一些上层人士,包括那些文人雅士,保持一种有一定友谊成分的此唱彼和的交往。这种妓女和嫖客的关系决不单纯是性交关系,而可能有一些志同道合的成分,甚至有爱情的成分。当然,这种高级妓女是很少的。
在秦、汉、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虽然私妓已经出现并较春秋时期有所发展,但由于这时商业经济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市民队伍还未形成规模,都市文化发展较为缓慢,所以虽然家妓在上层社会相当普遍,而在市井商业性的卖淫现象并不普遍,只是到了六朝时,当时中国最繁华之地江南一带的城市中,私妓才较为活跃。关于这一情况,《玉台新咏》和《乐府诗集》的一些诗中都有所反映。例如,有一首《襄阳乐》:“朝发襄阳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诸女儿,花艳惊郎目”,反映出当时这一地区私妓之盛。《浔阳乐》:“鸡亭故人去,九里新人还。送一却迎两,无有暂时闲。”
《石城乐》:“生长石城下,开窗对城楼,城中诸少年,出入见依投”,则反映出当时期客之盛,妓女们几乎是应接不暇。值得注意的还有一首《夜度娘》:“夜来冒霜雪,晨去履风波。虽得叙微情,奈侬身苦何?”前两句反映出那时的官僚、贵族也有嫖妓的,甚至皇帝也有留宿娼家的,(如梁简文帝《鸟栖曲》曰:“青牛丹毂七香车,可怜今夜宿娼家。娼家高树鸟欲栖,罗帷翠被任君低”,这是他私生活的写照。)不过他们往往是招妓上门侍宿,所以上诗所述的那位夜度娘才“夜来冒霜雪,晨去履风波”。南朝的沈约有一首《早行逢故人车中为赠》的诗:“残朱犹暧暧,余粉尚霏霏,昨宵何处宿,今晨拂露归”,也反映出一个送身上门的私妓的情况。《夜度娘》诗中的“奈侬身苦何”句,表现出当时的妓女身不由己、命如黄花的悲叹。
至于当时的嫖客,除了前引诗中所述的“城中诸少年”与少数官僚、贵族外,当以商人为多。这类人多行商飘泊在外,又有一些资财,往往以宿娼作为一种生活的补充。据释宝月《估客乐》二诗云:“郎作十里行,侬作九里送。拔侬头上钗,与郎资路用。有信数寄书,无信心相忆。莫作瓶落井,一去无消息。”“大媥珂峨头,何处发扬州。信问媥上郎,见侬所欢不?初发扬州时,船出妻津泊。五两如竹林,何处相寻博。”从诗意看来,语言似出一妓女之口,而所送所问的“郎”则是一个商人。当时,私妓在长江一带的城市中较为发达。开始出现了个别名妓女,甚至流传后世,这就是南宋、南齐时的姚玉京和苏小小。
梅禹金在《青泥莲花记》中记载:“姚玉京娼家女也,嫁襄州小吏卫敬瑜,溺水而死,玉京守志养舅姑。常有双燕巢梁间,一日为鸷鸟所获,其一孤飞悲鸣,徘徊至秋,翔集玉京之臂,如告别然。玉京以红缕系足,曰:‘新春复来,为吾侣也。’明年果至,因赠诗曰:‘昔时无偶去,今年还独归。故人恩义重,不忍更双飞。’自尔秋归春来,凡六七年。七年玉京病卒,明年燕来,周章哀鸣。家人语曰:‘玉京死矣,坟在南郭。’燕遂至坟所,亦死。每风清月明,襄人见玉京与燕同游汉水之滨。至唐李公佐撰《燕女坟记》。”看来在古人的记载中,认为姚玉京虽然是娼家女,但品德很好,文才也好,甚至感动了燕子。此事在《南史孝义传》上也有记载。
苏小小是“钱塘名娼,南齐时人,写有《西陵歌》。”所谓《西陵歌》是苏小小所写的诗:“妾乘油壁车,郎骑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出自妓女之手的诗歌,这可能是她私妓生活的写照。也可能是她对真正爱情的向往。她的墓在西子湖畔,一说在嘉兴,后人对此有许多诗文与传说,寄托了对这一代名妓的遐想与怀念。例如宋朝何蘧的《春渚记闻》中说:“司马才仲在洛下梦一美妾,搴帷而歌。……且曰:‘后相见于钱塘。’后才仲为钱塘幕官,廨舍后堂苏小墓在焉。……不逾年而才仲得疾,所乘画水舆曦泊河塘,舵工见才仲携美人登舟……而火起舟尾,仓皇走报,而娼家已痛哭矣。”
又如唐朝的徐凝作《寒食诗》云:“嘉兴郭里逢寒食,落日家家拜扫归。只有县前苏小墓,无人送与纸灰钱。”直到清朝,还有些文人雅士写诗怀念她,如朱竹坨诗云:“歌扇风流忆旧家,一丘落月几啼鸦。芳痕不肯为黄土,犹幻胭脂半树花。”这时,苏小小已离世千年,早成黄土,有些文人对她仍低徊不尽,可见其魅力与影响之大。“歌扇风流”等语,也正是她妓女生涯的写照。
以上所述的这些妓女,无论是营妓、家妓还是私妓,以及一些宫妓,其下场大都是较为悲惨的。其中只有极少数佼佼者能从妓女“攀龙附凤”,进入贵族阶层,如李夫人、赵飞燕等。当然,这是要有一定条件的:首先是由于貌美而被皇帝或其它大官、大贵族所宠;其次是要有一定的手腕以巩固主子的欢心,并在宫闱的勾心斗角中获胜;三是要有儿子,以及儿子最后能继位。以上三者缺一不可,汉武帝的宠妾李夫人对这点就看得很清楚,她对汉武帝说:“我以容貌之好,得从微贱受幸于上。
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爱弛则恩绝。上所以拳拳顾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有无儿子,儿子能否继位,更为关键。如秦时邯郸姬(秦始皇之母)、曹魏卞皇后(曹丕之母)、东晋安德陈太后(安、泰二帝之母)等都是母以子贵,儿子做了皇帝,她们的地位才算最后巩固。相反,赵飞燕虽被汉成帝立为皇后,“母仪天下”,但因为无子,在平帝即位后便被废为庶人,最后以自杀了此一生。
更多的妓女是从良,这是许多妓女十分向往的一种归宿,她们深知人生如朝露,红颜易老,当妓女不可能当一辈子,所以,在为娼时一有机会,就“择枝而栖”了。唐代名妓徐月英的《叙怀》诗:“为失三从泣泪频,此身何用处人伦。虽然日逐笙歌乐,常羡荆钗与布裙”,则反映出古代妓女的共同心情。妓女从良之事很多,例如魏武帝有一名宫妓名卢女者,擅鼓琴,后来被“放出嫁为尹更生之妻。”《古诗十九首·青青河畔草》中所说的“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也是这个意思。所谓“荡子”,不是指行为不轨之人,而是指经常离家外出的游士或商人等。当然,从良也并非一定幸福,所嫁非人、遗恨终身的事也常常发生。
如果从良不得或所嫁非人,年老色衰后陷于冻馁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出家为尼姑或女冠。佛教自两汉时传入中国,至南北朝时大为发展,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当时佛寺遍布山林,寺院不仅收纳大量男子为僧,而且也剃度不少女子为尼。当时,道教也有较大发展,女子也可入道为冠。当了尼姑或女冠后,生活就有了保障。所以,为尼为冠就成了当时不少妓女的归宿。
当然,妓女为尼为冠,也不完全是为了取得生活保障。有些妓女经历了多年风风雨雨、冷冷暖暖、爱爱恨恨的生涯后,看破红尘,决心和青灯古佛、大吕黄钟为伴,了此残生。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的僧尼经常举行宗教性的歌舞活动,既娱神也娱人,而这正好发挥了不少妓女的专长,寺院用得上她们,她们也还有用武之地。据《洛阳伽蓝记》卷一记载:“景乐寺……六斋常设女乐,歌声绕梁,舞袖徐转,丝管嘹亮,谐妙入神。以是尼寺,丈夫不得入。得往观者,以为至天堂。”就说明了这种状况。总之,古代的妓女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的歌舞艺术水平,这与后世是有很大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