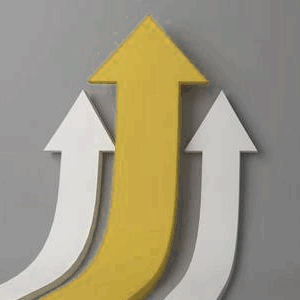野史八卦 王路:晚年杜甫写诗有多随意?
人们都说,写诗不能学李白,要学杜甫。李白是天才,天才是学不来的。杜甫靠努力,所以可以学。
呵呵。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写于开元二十四年,杜甫二十五岁。
唐诗中,这篇可以名列前茅。很多人努力一辈子,写不到这水平。
如果三十岁前写不出一流的诗,后半辈子也别想了。写诗不是做学问,不看积累,看天分。
杜甫早年的诗,十分精当。天才的英气咄咄逼人。到了晚年,变得随意了。
猛一看,似乎不如早年好。
仔细看,还是似乎不如早年好。
这时候,诗坛盟主站出来了:老杜晚年,怎么能写到如此境界!不可及,不可及!
大家恍然大悟:呦!原来是我辈学力不到!
这个诗坛盟主,就是黄庭坚。黄庭坚一说,大家都信了。又过了百十年,出一个大学问家,朱熹。朱熹怎么看,怎么觉得不对劲。他说那些黄庭坚的拥趸:你们啊,都是矮子看戏,个儿高的说好,你们就跟着叫好,其实你们啥都没看见。
朱熹和黄庭坚的分歧,饶宗颐有篇《论杜甫夔州诗》,仔细讨论了这段公案。我的看法和饶公有些出入,此文不细表,单表老杜晚年随意不随意。
朱熹说:杜诗初年甚精,晚年横逆不可当,只意到处便押一个韵。
读到这句前,我想不出如何评价杜诗初年和晚年的差别,读到这句,对了,就是这个味道,太熨帖。
“横逆不可当”,其实就是随便。——横着走,竖着走,斜着走,爱怎么来就怎么来。
一般人这么来,叫草率;但老杜这么来,不能叫草率,要叫横逆不可当。不过,你再横逆不可当,也得押韵,怎么办呢:“只意到处便押一个韵。”
我觉得,朱熹这句话里,丝毫没有对杜甫的贬抑。不过,很多人以为有。我们且不管,拿出诗来看看。
大历五年,老杜临死那年,有个表侄去南海,老杜写了首诗送他。诗很长,简单挑几句:我之曾祖姑,尔之高祖母。尔祖未显时,归为尚书妇。
明朝竟陵派诗人钟惺说:这是志和传记的格式,居然拿来写诗,真奇怪!还拿来当开头,真奇怪!
老杜中间写:次问最少年,虬髯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下云风云合,龙虎一吟吼。愿展丈夫雄,得辞儿女丑。
清朝的仇兆鳌,读到这里,皱起眉头:“太宗虬髯,恐非十八九岁所有,此亦讹传也。”
老杜后面又写:凤雏无凡毛,五色非尔曹。往者胡作逆,乾坤沸嗷嗷。
翻译成白话是:凤凰的种,那能是一般的毛吗?长了五色毛的人,除了尔等还有谁呢!当年安禄山那小子作乱,天下跟炸了锅似的嗷嗷叫。
再往后:自下所骑马,右持腰间刀。左牵紫游缰,飞走使我高。
“飞走使我高”的“高”,要说不是凑韵,没人相信。为什么不用“飞走使我逃”呢,因为“逃”字前面用过了。如果这首诗不是杜甫写的,换个人写,“高”就有毛病了。但它是杜甫写的,那就没毛病。
仇兆鳌说:“高字拈韵,或疑句稚,不知此正写真处,公方徒步蓬蒿,欲行不前,忽飞马高骑可以脱险,故不胜喜幸。”
意思是,别以为“高”是随手捡的韵脚,就觉得稚嫩,殊不知,这正是真实的写照。
仔细想想,也对,骑在马上确实比站在地上高。再想,恍然大悟:原来可以看成倒装——使我高飞走,哎呀,高字用得妙!
老杜晚年,到处是这样的诗。
随便看看吧。
《可叹》,写于大历二年末,离去世还有三年: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须改变如苍狗。
古往今来共一时,人生万事无不有。
近者抉眼去其夫,河东女儿身姓柳。
丈夫正色动引经,酆城客子王季友。
群书万卷常暗诵,孝经一通看在手。
……太守得之更不疑,人生反覆看亦丑……看起来很随意,但越咂摸,越有味道。通篇说的都是人话。老杜不是为了写诗才写诗,是为了说话才写诗。黄庭坚说,老杜写诗,没一个字没来历,后人以为是老杜的发明,只是因为读书少。黄庭坚比较爱讲夸张的话,不过虽然夸张,倒也对。很多地方,即便你不知道来历,也不影响。比如前两句,白衣苍狗,出自《晋书·天文志》。第四句,“人生万事无不有”,化用了嵇康诗“事故无不有”。
老杜不经意的下字处,都在考验诗的极限。后人学诗,如果有些句子想到了,不确定行不行,那就先看看杜甫。如果杜甫这样写过,那就是可以的。如果连杜甫都没有,这样写肯定不可以。
这不是开玩笑。不是黑杜甫。这是对杜甫最大的赞美。杜甫之于中国旧诗,是立法者的地位。诗圣,意思是,诗里的孔子。在诗的国度,杜甫定义了规则。
看杜甫突破的地方,就知道,有些突破也未尝不可。不仅是在选题取材上,甚至包括近体诗天生的规矩——格律。
“怅望千秋一洒泪”,就与“风流儒雅亦吾师”失粘。也许只是杜甫一时不小心。诗人往往有不小心的时候,李白也有,“吴宫花草埋幽径”就是。所以你就知道,如果不小心,失粘了,句子既佳,也不妨由它失粘。
甚至,有时候明明知道格律不对,硬要这么用,也不是不可以。比如,“白帝城中云出门,白帝城下雨翻盆”。既然老杜这么写,你写“叉叉门上太阳升,叉叉门前扫地僧”,人家也不能诟病。
如果后人没有读过老杜,偶然写出一句,碰巧与老杜一样,说明什么问题呢?
什么都说明不了。偶然几个字撞衫,并不难。
要褒奖一个作者,有句俗套话:“这东西,一看就是某某写的。”说明他已经有自己的风格了。但诚实地讲,难道杜甫的每一首诗,乃至每一句,都打着鲜明的“杜甫”烙印吗?
绝对是戏言。
曹雪芹有两句佚诗: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周汝昌补了前六句,骗人说不知道哪里看来的。吴世昌琢磨很久,认定就是曹雪芹原诗,洋洋洒洒写了很长的文章证明,然后乌龙了。出来两种议论,一种认为,吴世昌对曹雪芹还不够了解。一种认为,不是吴世昌不了解曹雪芹,而是周汝昌模仿曹雪芹太像了。
其实都不是。真正的原因是,根本没办法看出来。别说是曹雪芹,就是李太白的《蜀道难》,如果流传下来时没有李太白的名字,谁敢断定它就是李太白写的?
《秋雨吟》,“兼是孤舟夜泊时,风吹折苇来相佐”。杜甫集没有收,《事文类聚》说是杜甫所写,仇兆鳌研究了很久,说:“今玩其句调语气,酷似夔州夜归诗,俟从容详考也。”
“俟从容详考”,意思就是,这事我搞不定,没有足够的证据。仇兆鳌琢磨杜甫一辈子,也只敢这样说。这才是老实本分的态度。判断不了就是判断不了,想在一首诗上伪装一个人,没有那么难。
老杜之所以成为老杜,并不是看他某一两首诗,更不是看一两句。而是看整个杜甫集。
说杜诗有早年和晚年之分,夔州前和夔州后之别,也只是一种方便的说法。杜诗本身并没有那么割裂。不是说到了夔州后,诗风陡然一变。老杜自称,“老去诗篇浑漫与”。其实他年轻时也颇多漫与的诗篇,并不是每一首都“甚精”。朱熹说甚精,是指老杜初年的功夫,不是指篇篇皆精;说横逆不可当,是指老杜晚年的风格,也不是指处处皆横逆。不要把活龙当死蛇看。实际上,“老去诗篇浑漫与”这句,写于上元二年,老杜当时还没到夔州呢。
老杜诗中也有不怎么样的。比如《徐卿二子歌》,也写于上元二年:君不见徐卿二子生绝奇,感应吉梦相追随。
孔子释氏亲抱送,并是天上麒麟儿。
大儿九龄色清澈,秋水为神玉为骨。
小儿五岁气食牛,满堂宾客皆回头。
吾知徐公百不忧,积善衮衮生公侯。
丈夫生儿有如此二雏者,名位岂肯卑微休。
明末,河朔诗派领袖申涵光说:“此等题,虽老杜亦不能佳。今人刻诗集,生子祝寿,套数满纸,岂不可厌。”
就算是超一流的高手,随便应付一首诗,也照样平庸。不过,老杜晚年的“漫与”,和这种并不一样。这种是应酬之题,而晚年漫与,则是早已达到超一流境界后,反而不太关心诗的好坏。
总是憋着一股子气要让自己不朽的人,往往离不朽早影着呢。如果早就不朽,往后就很随意了,晚年的杜甫就是这样。但正是在这种“漫与”里,杜甫开出了诗的新境界。壮年的杜甫,很认真地写诗,已臻时代之巅峰——但尚未甄历史之巅峰,晚年他一恣意,就给旧诗画上了句号。
老杜的横逆,一方面体现在选材上。无论什么事,都可以拿来入诗。别人写诗,素材有限,老杜取材就宽广得多:送菜、送瓜、卖鸡,都写到诗里。同时代的人,除了少数有识之士外,大多看不懂这种远远超越时代的写法。诗歌的发展演变史终于证明,老杜不可及。
临终前一年,杜甫写《园人送瓜》,开头是:江间虽炎瘴,瓜熟亦不早。
有点啰嗦。“瓜熟亦不早”,很口语化嘛,两句可以并成一句,“江瘴瓜熟晚”。——要这样看,就是“作诗的人”了。老杜是诗人,不是作诗的人。到晚年,根本不带考虑什么技巧,什么用字。在他貌似的不讲究之中,有深深的讲究。人家年轻时就“甚精”了,对于诗,该懂的东西他都懂了,“诗是吾家事”。再写,就不是为了不朽,只是为了说话。“晚节渐于诗律细”,偏像形容初年的杜诗;“谁家数去酒杯宽”,才像晚年的老杜味道。
晚年老杜,好比早就天下第一的武林高手,在跟人谈论剑法时,随便捡支木棍比划两下,你真以为那种随手的比划中力道很强,很精妙吗?其实没有。那就是散漫的示意,没什么技击的效果。但正因为特别散漫,特别随意,蕴涵了十分精妙的境界。一旦着意,那种境界可能就跑了。
“晚节渐于诗律细,谁家数去酒杯宽。”对仗怎能如此随意呢,如何从诗律细想到酒杯宽呢。这种跳跃里,包含了最上层的武学。后人效仿,但十之八九都是在故作随意。
杜甫让僮仆去菜园子里摘菜,回头就写了《驱竖子摘苍耳》。还有《竖子至》、《槐叶冷淘》、《上后园山脚》,甚至诗题就一个字:《瞑》、《晚》、《夜》、《闷》、《雷》。还有《刈稻了咏怀》、《耳聋》、《楼上》。盗贼退了,写《喜闻盗贼总退口号五首》。
僮仆绑了鸡去集市卖,鸡被绑得咯咯叫,杜甫写《缚鸡行》:小奴缚鸡向市卖,鸡被缚急相喧争。
家中厌鸡食虫蚁,不知鸡卖还遭烹。
虫鸡于人何厚薄,吾叱奴人解其缚。
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倚山阁。
家人不喜欢鸡吃虫子,要把鸡卖掉,杜甫想到鸡卖掉会被杀了吃,不禁怜悯起来,让童子放了。但应该爱鸡多一点还是爱虫子多一点呢?不知道,只好遥望着寒江的倚山阁。末句的跳脱,不可想象。洪迈说:“《缚鸡行》自是一段好议论,至结句之妙,尤非思议所及。”
这种随意漫与的地方,其实是杜甫的天分所在,没有办法学。不仅李太白没有办法学,晚年的杜子美也没有办法学。朱熹讲的其实比黄庭坚老实,黄庭坚夸张,朱熹平实,他说杜甫“夔州以后,自出规模,不可学。”
就算后人学晚年的杜甫,偶然写出和杜甫一样的句子,也不高。这就好比你在没有了解牛顿定律时,偶然推导出了,也无从媲美牛顿的光辉。不过,物理学没有终点,爱因斯坦还可以推翻牛顿。但旧诗已经定型,没有人可能推翻杜甫。
而且,杜甫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取材上的开辟。任何有天分的人,只要放在合适的时代,有了合适的机缘,都有可能成为开辟者。杜甫的高度,还在于他在写实上绝无匹俦的勇猛功力。凭想象来写诗,比较容易,但真要把眼前景物心绪栩栩历历地落到纸上来,就难了。黄庭坚离了贵州,诗风变得笃实,也是学杜精进的体现。
杜甫写“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就好。你这样写,就假。因为你家隔壁没有住着黄四娘,门口也没有千朵万朵的花。过了杜甫的时代,离了那个因缘际会的时空,就不可能再有杜甫了。这才是杜甫之所以后无来者的原因。
旧诗的王国里,本来没有路。杜甫走到哪儿,哪儿就有了路。
杜甫给旧诗画了句号,定义了旧诗的界限。所有变化之能事,杜甫都指出了方向。后来的诗人,所有的努力,都只为在杜甫既定的地盘里,讨一碗羹,琢磨些零碎的突破。
晚年的杜甫,只有一个作用,就是让人知道诗还可以写到这个地步。
杜甫的晚年,是用来景仰的,不是用来学习的。
杜甫之前,没有这样的高度,之后也永远不会有。
杜甫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