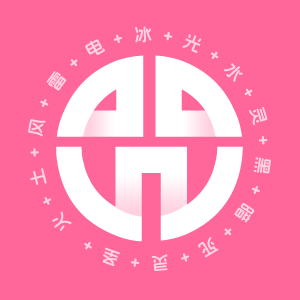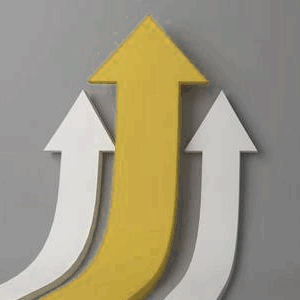从“作品”到“说话”:建构数字时代的大文艺观
摘
要:在社交媒体时代,大众文艺评论等互动活动成为文艺消费的内容,评论者需要摆脱作品中心主义,建构涵盖“作品”与“活动”的大文艺观。数字时代的大文艺观与人们时常提到的“大文艺”观有两点不同,一是将作品外的“活动”包括在内,二是“作品”与“活动”并非机械叠加,而是被交流所贯穿,成为一条条话题素,不再有作品内外的区别。中国传统的“说话”概念可有效涵盖数字时代大文艺观中“作品”与“活动”的二重性。同时,这构成了一种SNS社区式集体生产,既承认了传统的著作权,又体现了网络的开源精神。在文化参与的背后,我们也需要注意到数字资本主义的文化生产逻辑走向了精神政治。
关键词:社交媒体;大文艺观;“说话”;精神政治
新媒介对文艺评论造成了剧烈冲击,学院评论不再一家独大,大众文艺评论崛起。尽管在符号资本上大众文艺评论与前者不可同日而语,但随着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对日常生活的深刻影响,其力量不容小视,突出表现就是弹幕文化的兴起。动漫、电影、游戏、音乐、文学等几乎所有的文艺样式都有了弹幕,文艺消费变成了盛大节日,人们已经习惯在群体评说中共同欣赏,并在集体交互中获得共鸣与温暖。社交媒体时代,大众文艺评论已深刻改变了文艺的生产、传播与消费模式。
一、数字时代的大文艺观:“作品”与“活动”的交互
社交媒体时代大众文艺评论的爆发,带来的重要变化就是评论成为文艺内容,人们开始由“追剧”“追文”走向“追评”。新媒介语境下的文艺消费与传统文艺消费的不同,在于它消费的并不只是作品本身,还包括互动体验。这种差异在新媒介文艺刚开始兴起时就体现出来,读者的阅读快感既源于欣赏故事,也源于阅读评论。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评论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以网络小说《大王饶命》为例,整本书几乎变成一个论坛,读者在里面评论剧情、谈天说地,把互动性体现得淋漓尽致,其中一些神评论,会引来读者大量回复,其质量甚至高于作品本身。网友们对这些评论也看得兴致勃勃,网友“欧文子”这样说:“现在看小说根本停不下来点击本章说的手,以前只能在文章末尾的时候还好,现在每句话后面都有本章说,我的手根本停不下来,每条本章说都忍不住看过去并且点赞。花在看本章说上的时间比看正文还多,以前看过的书还要再回去看本章说。”[1]这里提到的“本章说”,有些网站又称“间帖”,实际上就是文学版的弹幕。有网友甚至表示评论才是本体,“没了本章说就像菜没放盐,以前一章可以看十多分钟,现在三分钟”[2]。
看评论显然会影响故事欣赏的流畅性,但伴随社交媒体长大的“Z世代”热衷于这种边看边聊的断续模式,这构成对印刷文化线性模式的解构,也出人意料地让文艺欣赏变慢,改变了固有的刷屏模式。这种以评论为基础的文艺欣赏的时空结合体,跟以前的媒体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社交媒体时代以评论为中心的互动构成文艺体验的重要内容,客观上要求反思印刷文化语境的作品中心主义,将作品外的互动活动视为文艺的一部分。
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过,社交媒体带来的广泛聊天互动表现的就是媒介理论家沃尔特·翁所说的“次生口语文化”(secondary
orality),这是继“原生口语文化”(primary
orality)之后新的口语文化。[3]麦克卢汉的“媒介四定律”认为,媒介总是会放大、遮蔽、再现社会生活的某个方面,或逆转为其他东西。[4]莱文森也提出“补救性媒介”(remedial
media)的说法,认为媒介演化历史是一种补救过程,后兴起的媒介往往是对前面媒介的改进。[5]在社交媒体时代,次生口语文化勃兴的意义在于,它构成了逆向再现或“补救”,释放与重建了被印刷文化压抑的文化可能性。
对于文艺评论来说,被印刷文化压抑的是什么呢?在笔者看来,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作品外的交互活动。随着印刷文化语境中文艺的案头化、精英化,我们形成以“作品”为核心的思维模式,与这种思维模式相适应的文艺审美方式就是静观。对于社交媒体语境下的文艺欣赏来说,我们需要重视作品外的活动。既然它表现的是次生口语文化的后果,那么我们结合口头传统可能会看得更明白。
传统研究经常错误地以文本去理解口头传统,按照美国民俗学家阿兰·邓迪斯(Alan
Dundes)的说法,这种倾向甚至表现在代表性学者帕里、洛德的口头程式理论中。尽管他们在南斯拉夫的田野作业是演述理论的先驱,但口头程式理论在方法上侧重对史诗不同文本的比较考察,以确定其程式与主题,因而“将侧重点放在文本上而非语境上”[6]。但准确地说,不能把口头艺术等同于文本或作品,而应将其理解为“演述”(performance)。“performance”这一概念在口头传统研究中的运用,来自洛德《故事的歌手》中提出的“演述”(performance)与“创编”(composition)的关系。[7]国内民俗学界一般将其译为“表演”,但“表演”容易被“狭隘地理解为‘舞台上的表演’”。[8]而口头艺术的演述主要是指互动交流与“言说方式”(a
mode
of
speaking)。哈佛大学教授格雷戈里·纳吉(Gregory
Nagy)指出,他对“演述”一词的使用,无意于传达任何有关舞台表现(stage-presence)的意涵;而强调的是其语用学效应。[9]在此基础上,我国学者巴莫曲布嫫主张采用“演述”这一译法,以替代通常概念上的“表演”。[10]演述理论深受言语行为理论的影响,也受到交流民族志(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的启发。也就是说,作品之外的语境、交流活动需要进入评论的视野,从“以文本为中心”转向“以演述为中心”,对口头传统的理解由一种“事物”(文本、事象、精神产物),转变为一种现场、语境的“行动”与“交流方式”。我们对次生口语文化语境中的新媒介文艺也应如此理解,不能只是将它理解成一个作品,而应把情境性的说话行为作为考察的重点,强调文本与语境的相互依赖关系。由此,艺术事件、情境或场景,讲述人与听众之间的互动,文本在交流中动态而复杂的形成过程等,成为文艺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学者已经在反思“作品中心主义”,如高小康认为,传统研究是以作品为中心的,在对象、目的、范式与方法四个方面的核心就是文本,这似乎具有理所当然的正当性,但遮蔽了文本外许多活生生的文学经验,为此他提出“非文本诗学”的说法,主张在研究对象上从文本向活动的扩展。[11]高小康的说法是就传统语境而言,联系到数字时代文艺活动要素得到前所未有的凸显,“非文本诗学”对于我们转变文艺观念具有重要意义。在高小康的研究基础上,我们可推进这一问题的探讨。
笔者认为高小康的观点还有两点不足。一是他虽然强调“以活动为对象”,但侧重的是还原文学文本发生和传播的活态过程,以认识文学意义生成的生态根据。然而,在社交媒体语境下,以评论为主导的交互活动并不只是意义生成的根据,而是具有了独立审美价值,显然,我们也应该把活动视为文艺内容。二是“非文本诗学”这一提法不够严密,容易让我们忽视作品。这种倾向也体现在人们对次生口语文化的理解中,沃尔特·翁虽然提出“次生口语文化”,但侧重的是口语文化的遗存(Oral
Residue)。[12]这实际上也是不少学者口语文化研究的思路,即从口语文化到“书写—印刷”文化的历史转变并不是一种断裂,而是呈现为口语文化的韧性,需要注意口头传统在印刷文化大一统过程中的“抵抗”与“遗留”。[13]但笔者认为,如果只是从“遗存”角度来理解次生口语文化,将其视为口头传统的残留物,就很容易抹杀新生口语文化的特点。次生口语文化毕竟是“次生”的,经过印刷文化的中介,不能将其与口头传统完全等同。在社交媒体语境中,我们需要重视作品外的活动,但也要重视作品本身,两者应结合起来研究,建构一种能够涵盖“作品”与“活动”的“大文艺”观。
关于“大文艺”观或“大文学”观的说法已经很多了,笔者所说的数字时代的“大文艺”观与之前的说法有以下两方面重要而显著的不同。
一方面,传统“大文学”观忽视了作品外的活动,主要强调的是从文学研究走向文化研究,或者从“纯文学”观念转向中国传统的“杂文学”观念。这种观念对于数字时代“大文艺”观也有启发意义。数字时代各种博客、日志、短信写作、非虚构写作等,难以用“纯文学”观去容纳,同时文学、动漫、影视、游戏等新媒介文艺形式也彼此相通,难以截然分开,因此有必要重建中国传统的“杂文学”观念,从宽泛意义上去理解作品,将其视为“大文艺”观的内涵之一。但是,这种“大文学”观深受印刷文化的“作品”视野的限制,只是从纯文学作品扩展到了非文学作品,而忽视了作品外的活动。
另一方面,本文提出的数字时代的大文艺观所主张的“作品”与“活动”相结合,并不是指两者的机械叠加,而是强调在社交媒体的作用下,作品与作品外的活动已经交互在一起,这种交互是一种动态的拆解与贯穿。例如,弹幕是针对作品中一个个剧情片段展开的,拆解了作品。而受此影响,作者在文艺生产中也开始强调“弹幕思维”,有意在作品中营造一个个可供消费者吐槽的剧情点。从结构层面看,作品与作品外的评论已没有本质区别,它们都被社交媒体的交流所贯穿,沦为一个个话题素,它们已融为一体,不再有作品内外的差异,这是数字时代文艺对象前所未有的结构性变迁。
二、从“作品”到“说话”:文艺理论中国话语的建构
从社交媒体时代大众文艺评论的这种独特性可以看出,新媒介文艺实际上是一种活态文化。因此,我们既需要反思“作品中心主义”,也需要反思源自西方的作品、文本观念,进而建构新的文艺理论中国话语。在笔者看来,我们可以激活中国传统的“说话”概念,将新媒介文艺理解为类似于古代“说话”的活动,这一概念能够较为清晰地揭示出数字时代“作品”与“活动”的双重关系。
著名汉学家浦安迪曾激活中国传统的“说话”概念,以此来理解中国的叙事文。不过他将“说话”理解成“小说的成品”,仍是从“作品”意义上去理解“说话”,这与他深受西方叙事理论的影响,并为寻求可比性而“以中就西”的思维方式有关。比如,他还将叙事理论中的“叙述者”等同于“说话人”[14],但两者显然存在重要区别:叙述者是文本中的话语,“说话人”则置身于故事外部,指向的是现场的说书活动。“小说的成品”与“说话”同样存在这种差异,这是口头与书面两种文学与两种传统的区别。
中国传统的“说话”概念包含着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话本,即说话艺人用以“说话”的底本;二是“说话”这一活动本身。鲁迅曾对平话有这样一段议论:“观其简率之处,颇足疑为说话人所用之话本。由此推演,大加波澜,即可以愉悦听者,然页必有图,则仍亦供人阅览之书也。”[15]这段话表明话本有两种发展走向,一是指向案头阅读,即“供人阅览之书”,也就是发展为书面文化;二是指向现场的“说话”活动,即“说话人所用之话本”,“由此推演,大加波澜,即可以愉悦听者”。这两种走向跟新媒介文艺“作品”与“活动”相交互的二重性是一致的,我们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来理解。
一方面,从作品与活动相交互的大文艺观出发,我们可以先将网络文学等新媒介文艺理解成作品,肯定其具有书面或案头文化属性,是“供人阅览之书”,但又不能简单地将其等同于传统印刷文化,而应将其视为一种类似于说书的“话本”。这种类似于说书的“话本”,实际上就是一种“底本”或“手稿”。从印刷文学的标准看,它在艺术上可能比较粗糙,如果要将它转换成纸质出版物(印刷文学),需要一个文人化的提升,这与说书等活态艺术案头化的历史过程相通。同时,这种艺术的“粗糙”,可能只是从书面文化观察的结果,而并非真正的“缺点”。这种“缺点”实际上与现场交流的需要有关。
这个问题涉及文学史价值的重新评估。胡适曾认为西洋小说谨严统一,而中国小说“差不多都是没有布局的”,即便如《金瓶梅》《红楼梦》者,“结构仍旧是很松的”。[16]这也是近现代知识分子在中西比较视野中的普遍看法,如陈寅恪也认为:“至于吾国小说,则其结构远不如西洋小说之精密。”[17]这种评价与一些西方汉学家对中国小说“缀段性”的消极评价相似。[18]但中国小说这种结构特征实际上与中国的说书传统相关,复杂紧凑的高潮结构是书面文化发展的结果,松散结构与活态文化在文本中的遗留有关,是适应现场演出的需要:“口语文化里的叙事者在松散的场景模式里活动。”因此,也很难说松散结构就是艺术上的失败,这种结构在西方小说中也存在。从中世纪传奇故事一直到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借助主人公的游历把松散场景串联起来,表现的是“口头叙事世界迟迟不肯退场的鬼魂”[19]。如果只是从书面文学或文本本身来看,难以看出渗透其中的活态文化特性。
口头传统依赖记忆,因此口语化的故事在流传交互中不可能永恒不变地保存下来。“既然没有一个固定的文本来矫正,那么,变异就永远会悄悄地溜进来,部分是由于遗忘,部分地是由于改进、调整和创造的不自觉的企图。”[20]在印刷术出现之前,作品的形态是手稿,而手稿是变动不居的,“还比较贴近口头表达那种有来有往的特点”。与之相比,印刷文本是桀骜不驯的,“印制出来的文本绝不可能再做改变(删除、插入)”[21]到了网络时代,数字化让文本重新获得变动性。这导致新媒介文艺跟口头艺术一样,总是处于变动之中,这是新的文艺存在论。由于新媒介文艺类似于手稿或底本,它天然地具有这些文本变动不居的特点,这揭示了新媒介文艺“作品”层面不同于印刷文学的动态性。不过笔者这里所说的动态性与交流情境有关,由于弹幕等作品外的活动已成为文艺内容,作品与活动都被交流所贯穿,成为一条条话题素,因此,随着评论的不断加入,网络文本不断生长。这并不只是单纯量的叠加,而是每一次回应与互动都改变了文本整体的存在状态,构成新的情境,成为永未完成的开放叙事。
另一方面,“说话”指向的又是一种活动。社交媒体时代的文艺不能仅仅理解为一个“话本”,还需要将其看成一种活动。文本或作品难以替代现场活动的丰富体验,新媒介文艺不是静止的客体世界,而是进行中的事件世界。这也说明,从数字时代的大文艺观出发,除了关注作品,还要关注作品外的评论等活动,进行立体性研究。这种研究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研究文艺活态现场的文艺经验价值,以及虚拟社群对审美体验的生成作用,这类似于文艺地理学的研究思路,但拓展的是其虚拟维度;二是研究后续的各种衍生活动,具体包括线上线下、跨媒介、跨国界的生产、改编与传播行为,这构成更大的文化文本语境。
在研究方法上,“大文艺”观强调研究者摆脱以诠释文本为中心的传统方法,走向文本阐释与田野考察的结合。相比传统田野考察,这种研究应采用网络民族志与线下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民族志研究在数字时代有其必要性与优势[20],文艺活动在数字时代变得相当频繁,相比传统的无形文化空间,网络上现场的活态文化,通过各种帖子、留言得到事无巨细的记录与保存。[23]普通人的心态史、日常生活是西方年鉴学派、文化研究关注的重点,传统研究只能依据脱离现场的文本,数字媒介却为这些研究提供了便利。
通过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借用中国传统的“说话”概念,我们可以有效理解社交媒体时代的文艺活动,这可视为对文艺理论中国话语的当下建构。
三、文艺的SNS社区式集体生产
在数字时代的大文艺观视野下,文艺生产机制也发生了变化,变成了一种SNS(“Social
Network
Software”的简称,指社会性网络软件)社区式集体生产。SNS社区的本质是指通过网民共同的兴趣爱好发展社会关系,SNS社区式生产指内容的生产基于网民的社交关系与群体贡献。
福柯把作者界定为话语的功能,而不是话语的主体,作者的功能在整个话语中并不具有永恒、普遍的意义。从口头传统来看,这是实际情况。口头艺术往往是集体创作,将其归功于某一位文化英雄是十分常见的错误。随着印刷术的发展,“作者”的重要性开始得到凸显。一方面,印刷文化有利于个人表达,并带来了整齐划一的个人风格,在此基础上,“‘文人’遂应运而生”[24]。另一方面,印刷文本的线性排列、物质稳定性与读写的空间隔离,也促成了个体的批判意识与独立思考,提升了作者、知识分子和理论家的权威。[25]
网络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作者,形成类似于口头艺术集体创作的特征。常见的集体生产有三种情况:一是不同作家对一部作品的合作,如早期网络文学的接龙游戏;二是在网络流传中不同作家对同一部作品的修改;三是新媒介文艺如网络类型小说形成了集体的套路生产。这三种情况都类似于口头传统根据套语、程式等“预制件”的现场创编。第一种情况作为文学实验有其价值,但缺乏现实性,接龙写作往往半途而废。后两种情况具有相似性,都是基于原有共同设定、要素而做出的新创造,它们代表一种新的文艺生产关系,更具有理论探讨意义。
储卉娟认为这种新生产关系相当重要:“我们就进入了一场正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关键讨论。这场讨论以知识产权制度变革为核心命题,重新评估互联网技术所激发的文化潜能。”[26]言下之意是说,基于共同设定或套路的生产体现了网络共享文化,有可能突破印刷文明的私有化,形成人类社会新的知识生产与联合方式。这一说法似乎有些夸大其词,传统文艺也存在套路的互相借用,但在以前并未成为一个重大问题。
借用福斯特(M.
D.
Foster)的理论,可以深入理解这种新的创作状况。福斯特将流行文化对民俗产品的运用分为改编、精确用典(民俗主义)与模糊典故(类民俗整合)三种方式。改编与民俗主义对典故的运用容易辨识,要求作者和读者熟悉先行文本;“类民俗”则是模糊用典,需要作者和读者“熟悉共享的知识体系”,[27]这种知识体系就是人们所说的设定。面对无限的互文,约定俗成的东西已无从溯源,各种套路、设定成为共有财产,网络文学界常见的“融梗”“抄袭”指控似乎已没必要,这是以印刷文化的著作权来要求新生产模式的误置。这种讨论有些道理,但也有夸大之嫌。忽视作者的著作权,文化生产的创新动力难以持续,也变相地为时下新媒介文艺抄袭的不正之风张目。现在毕竟不是缺乏著作权意识的口头文化时期,而是经过了印刷文化中介的次生口语文化时代,作者的原创及著作权仍需肯定;但同时也不能忽视网络带来的集体生产的可能性。
从前面论述来看,社交媒体促成了一种新的集体生产模式,即作者创作的故事提供了基本话题,但更多内容需要网友在交往中来填充,而作者也会根据网友的填充而调整,在这种循环交互中构成了源源不断的合作生产,这正是“知乎”等基于社交关系的SNS社区内容生产模式。笔者曾把这种新的生产模式称为“维基百科式的联合生产模式”[28],现在看来并不十分确切。尽管它的内容生产原理也是如同维基百科那样依靠无数网友的集体贡献,但维基百科并没有突出社交关系,而社交关系才是当下文艺内容生产的动力与源泉,因此称其为“文艺的SNS社区式集体生产”或许更合适。同时也要注意到,以前人们对集体生产表示怀疑,认为这会导致作品主题与结构混乱不堪,典型的如接龙小说。但这是一种错误的思维定式,在社交媒体语境中,集体生产已经摆脱了“作品”的限制,它不需要统一的线索,文艺内容是由大量拼贴的、碎片化的话题素组成。
文艺SNS社区式集体生产模式的意义在于,它不是储卉娟所说的在网络文化的分享/合作与印刷文化的占有/个人之间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结合的可能,既承认了作者著作权,提供了文化生产的动力,又释放了受众联合生产的潜能,体现了网络的开源精神。故事文本的确表现了作家的著作权,但由不计其数的网友创作并在不断生长的弹幕,却很难说是某个人“拥有”的,也是不可能拥有的:“谁真正‘拥有’互联网的电子公告版上文本的权利并因此对之负责:作者、体系操作者还是参与者的社区?”[29]
在这种SNS社区式集体生产中,交往媒介应被视为文艺活动的要素之一。在现代传媒强势介入文艺活动的今天,学者单小曦提出在传统“世界、作家、作品、读者”四要素之外,增加“传媒”作为第五个要素。[30]考虑到当今传媒对文艺活动的深刻影响,将“媒介”视为第五要素是很有必要的。从媒介这一要素出发,在社交媒体时代应充分注意交往媒介在文艺活动中的重要性。在传统语境中,往往先有一个写好的作品供个人欣赏,交往媒介的作用尚不突出。在社交媒体语境中,更多内容需要受众在交往中生成,只有搭建了交往媒介后,这些内容才能持续不断地生产出来。比如在当下文艺评论中,弹幕就是一种交往媒介装置,它是内容生产的基础设施,起到“触媒”作用。当弹幕被引入作品时,作品就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变化性,引发网友贡献无穷无尽的内容。在今后的文艺活动中,应重视交往媒介的构建,因为这决定了文艺生产、文艺生活的性质与水平。
四、从生物政治到精神政治
文艺的SNS社区式集体生产充分表现了受众的主体性与文化参与,它与Web2.0以来的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用户生成内容)的网络文化精神相一致。Web1.0的特点是自上而下的“发布”;Web2.0的特点则是“参与”,赋予用户更大的主动性,依靠网友的群体贡献进行内容生产,社交媒体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文化精神。关于这种文化生产,国外也有“交往资本主义”“产消者资本主义”的提法。但从马克思主义视野看,这表明社交媒体时代资本主导下的文化生产逻辑发生了深刻变化。
英国思想家齐格蒙特·鲍曼曾经低估社交在资本生产中的作用,他认为后现代社会是购物社会,早期带有乡愁性质的拱廊街已让位于大型商场,这些公共空间“鼓励的是行动,而不是‘互动’”,因为“聊天和社会交往”妨碍了“购物的愉悦”。[31]但结合前面论述来看,鲍曼的说法可能需要改写,或者说正好相反,利用社交媒体,促成并鼓励用户之间的互动,是新媒介时代重要的商业策略。以游戏为例,游戏社区延长了玩家决定注销和离开的时间。它涉及所有类型的人与人交流,有时会超越虚拟世界的关系。玩家在游戏社区的“生存”时间常常要长于游戏对局,也就是说,社区的互动甚至比玩游戏本身更重要。因此,在设计游戏的时候,重要的关注点应在于积极营造游戏社区,并“提供所有的交流渠道”,如公告板、电子邮件、即时聊天系统,甚至视频会议。[32]从实际情况看,玩家在游戏中的聊天互动成为重要的现代生活内容,并深刻影响了玩家的个人生活与心理结构。这种互动不仅仅是一种社交需要,在社交媒体作用下,它也构成了内容的集体生产。从数字资本主义的视角看,这正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理念,体现了资本生产方式从生物政治走向精神政治。
德国哲学家韩炳哲对福柯的规训权力进行了反思,认为规训权力主要是一种生物政治,虽然福柯提到的全景监狱不局限于肉体,也对个体道德进行了改造,但总体来看,精神并非规训权力关注的核心。与之相比,新自由主义更依赖灵魂,精神政治是其统治形式。在此之前,斯蒂格勒已认识到福柯的生物权力概念在当下有些不合时宜,精神权力的心理技术正在取代生物权力,不过他理解的精神权力是指电视等远程节目让人们成为被欲望操纵的消费客体。在韩炳哲看来,斯蒂格勒对电视节目的过度看重是有问题的,他几乎没有研究过互联网、社交媒体,由此错失了广泛依赖数字技术的新自由主义精神政治学这个领域。[33]也就是说,数字媒介真正体现了新自由主义理念。
我们借助韩炳哲的观点,结合文艺SNS社区式集体生产模式来看,从生物政治到精神政治的转向包括从身体到精神、从否定性到肯定性、从外在视觉到内在无意识三个方面的变化。
福柯的规训机制施加于个体身体之上,是以作为机器的肉体为中心而形成的,构建了关于人体的生理常规管理,它在终极意义上仍是肉体政治学。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福柯从“规训权力”走向“生命权力”,关注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寿命、健康状况,强调对生命的监视、干预、扶植、优化与调节,但这仍是社会意义上的身体,是以人口统计学为基础的安全技术。从文艺的SNS社区式集体生产来看,它侧重的是精神政治。在弹幕引发的集体哄笑或共鸣感中,现代社会原子化的个体获得了温暖。它是大叙事终结后“想象的共同体”的替代物,是一种“情绪资本主义”。
福柯的规训权力仍受到否定论的控制,包含了禁止、压抑的侧面。尽管生命权力也注意到生产性,但主要还是规范化、规则化意义上的“生命管理”,而新自由主义的权力技术更加微妙而精明,它强调肯定性,借助社交媒体时代人们的主动性与UGC生产,激发其参与热情。如果有网友发出了“神弹幕”,会引起众多的点赞与叫好。它不是打击灵魂,而是向灵魂示好;它不用“苦药”,而是通过“点赞”来实现目的。动力、项目、竞赛、优化与倡议成为当代资本的治理术,生产不再是以异化的方式进行,而变成了自由和自我实现。
规训权力依靠视觉的凝视与规训,全景监狱与视觉媒介有关,在此意义上,规训权力的矫正技术比较粗糙,无法突破个体隐藏的愿望进入更深层的精神层面并侵占它。精神政治则依赖于大数据,可以破译人的内心世界,预测人的行为,使未来变得可控。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政治动物,但在网络社会中,人成了数据动物,网友集体生产及日常行为留下的无数网络痕迹就是大数据。大数据往往是不经意留下的行为轨迹,是人无意识的外化,通过大数据分析,能真实地描摹出人物的内心肖像。福柯也强调人口统计学,不过人口统计的记录并不是精神活动的记录。“人口统计无法对精神活动进行推断。在这点上,统计学和大数据是截然不同的。大数据不仅能刻画出个人的,也能刻画出群体的心理图景,也就可能对潜意识进行心理刻画,因此可以照亮心灵深处,从而实现对潜意识的利用。”
[34]
全景监狱体现的是从外部监控个人身体的视觉主义,大数据则让个体的外在肉体与内在灵魂都无所遁形。大数据并不只是数据,而是蕴含着重要的商业价值。由于做到了对无意识的清晰把握,它可以向个体精准推送内容。这样既提升了广告价值,也让受众投入的热情更大,因为推送的内容不再是消费社会培育起来的虚假欲望,恰好是个体涌动在心头与指尖的真正需求。这样就带来一种互相强化的效果,一方面,在迎合心意的推送下受众会积极生产内容,而这种生产构成了免费的数字劳动;另一方面,这种积极生产又会生成新的大数据,由此促成新的推送与生产,最终驱使主体不断投入奔忙与奋斗的人生。按照韩炳哲的看法,这就是现代功绩社会的主体命运,新自由主义主体“因自我优化,即因被迫产出越来越多的成绩而走向衰亡”[35]。
文艺SNS社区式集体生产体现了从生物政治到精神政治的变迁,这种转变与当下资本主义非物质、非肉体的生产模式是一致的:“今天的资本主义是由非物质和非肉体的生产模式所确定的。被生产的不是物质的,而是像信息和计划这类非物质的东西。作为生产力的肉体再也不如在生物政治性规训社会里那么重要了。”[36]韩炳哲的说法虽然有悲观和夸大的成分,但提醒我们注意数字资本主义的文化生产逻辑。
参考文献
[1]“欧文子”:《本章说比正文还有意思!》,http://www.lkong.net/thread-2301161-1-1.html,2019年4月29日。
[2]网友“火雀”等对本章说的讨论,http://www.lkong.net/thread-2332916-1-1.html,2019年6月6日。
[3]黎杨全:《走向活文学观:中国网络文学与次生口语文化》,《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10期。[4]McLuhan,
M.
McLuhan,
E.
Laws
of
Media:
The
New
Science.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8,
p.7.
[5][美]保罗·莱文森:《软利器:信息革命的自然历史与未来》,何道宽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0—98页。
[6]参看[美]阿兰·邓迪斯为约翰·迈尔斯·弗里《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朝戈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一书所写的“编者前言”第37页。
[7]"For
the
oral
poet
the
moment
of
composition
is
the
performance"(对口头诗人来说,创编的时刻即是演述),See
Chapter
2:
Singers:
Performance
and
Training,
in
Lord,
Albert
B.
The
Singer
of
Tal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p.12.
[8]杨利慧:《语境、过程、表演者与朝向当下的民俗学》,《民俗研究》2011年1期。
[9][10]参看[匈]格雷戈里·纳吉:《荷马诸问题》,巴莫曲布嫫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3页注释16、第330页。
[11]高小康:《非文本诗学:文学的文化生态视野》,《文学评论》2008年第6期。
[12][19][21][美]沃尔特·翁:《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语词的技术化》,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23、113—114、101页。
[13]黄海英、黄继刚:《场所、伎艺和民俗:“书会”的文化演进及意义递嬗》,《湖北民族大学学报》2021年第3期。
[14][18]参看[美]浦安迪:《中国叙事学》,陈珏整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8—19、56页。[15]鲁迅:《鲁迅三十年集·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出版社,1947年,第134页。
[16]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报馆,1924年,第70—71页。
[17]陈寅恪:《论〈再生缘〉》,《陈寅恪集·寒柳堂集》,三联书店,2001年,第67页。
[20][英]杰克·古迪:《口头传统中的记忆》,户晓辉译,《民族文学研究》2005年第1期。
[22]王晴锋:《概念民族志:基于欧文·戈夫曼的探讨》,《湖北民族大学学报》2021年第4期。
[23]张福强、高红:《“采集民族志”在中国的实践》,《湖北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
[24][美]麦克卢汉:《理解媒介》,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26—227页。
[25][美]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范静哗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84页。
[26]储卉娟:《说书人与梦工厂:技术、法律与网络文学生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4页。
[27][美]福斯特:《类民俗的迴圈:模糊用典以化成明日之俗》,陈征洋译,《东方文化学刊》(同人志)第8期。
[29][英]齐格蒙·鲍曼:《后现代性及其缺憾》,郇建立、李静韬译,学林出版社,2002年,第197页。
[30]单小曦:《论五要素文学活动范式的建构》,《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1期。
[31][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151—152页。[32][美]弗里德里:《在线游戏互动性理论》,陈宗斌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31—134页。[33][34][35][36][德]韩炳哲:《精神政治学》,关玉红译,中信出版社,第36、30、42、33—34页。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数字资本主义与新媒介文艺的转型研究”(21AZW002)。
作者简介
黎杨全,男,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