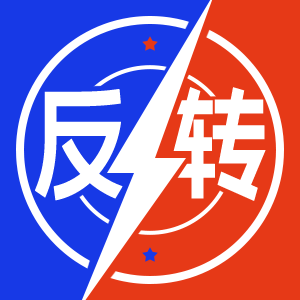副本模式、游牧身体与生命政治新范式
摘要:“后人类境况”的产生引发了当代科幻文艺生命伦理和审美范式的变革。网络科幻小说的叙事实践则是这种变革的话语表征。网络科幻小说在“反人类中心主义”叙事伦理的支撑下所构建的后人类生命形式、“游牧身体”体验、生命伦理观与生命政治学,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文艺审美活动对于现实社会治理模式与组织规范体系的一种“虚构性预演”或“想象性建构”。网络科幻小说借助于这种建基于科技与人性、生命与政治、审美与社会关系等维度之上的冷静思考与批判,充分地发挥了科幻文学以“技术狂想”、“后人类叙事”和新思维范式来反映、干预和改造现实社会中人类自身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此承载“科幻现实主义”的叙事正义与艺术伦理,呈现出符合时代特色的审美价值观与方法论,构建科幻文艺生命政治学的理论话语体系。
关键词:副本模式;游牧身体;生命政治;中国网络科幻小说;“后人类叙事”
一、科幻精神与网络科幻小说
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代社会,科幻文学的重要性日益明显,科幻文化则代表着时代的先声。经典科幻文学是基于一定科学技术基础上对人类自身以及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或合理或不合理的推测或假想,它通过投射、推论、类比、假定和阐释等言说方式,建立某种与传统叙事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话语秩序,并在它们所构建的文本体系中刻画和描摹特定的人物角色,叙述他们通过科学观察、假设或实验来对某种时空环境里的事物或情境进行探索、发现、甄别和验证的过程,呈现出一种超越经验世界的虚幻现实。[1]因此,“科幻是一种开放、多元、包容的文类,并不是只有所谓的‘硬科幻’才是科幻,真正的科幻不分软硬,它们都是基于对或然情境下人类境况的推测性想象。”[2]
科幻文艺对于未来世界或“后人类境况”的“寓言性建构”是将现实生活的隐喻体系编码成想象力的象征结构,以此揭示人类的现实生存境况,其用意在于将现实生活纳入到特定的阐释、表征和批判话语范畴之中。“后人类境况”的现实语境刺激了科幻文艺审美范式的变革,并最终引发文艺工作者关于人类生命实践之未来向度的叙事编码与想象。
此外,科幻文艺还可以穿行于任何可能性的时空关系中,自由地探讨各种科学问题、社会趋势与生命观念,如通过技术设想来探讨解决现实矛盾的方法,书写“拟真性”的历史状况,展现由多元生命价值观统摄的宇宙社会生态等,以此来揭示社会文明的发展变化,“阐明人类和其他族群及世界的关系”[3](P.11),揭示人性的深度与生存的价值。因此,科幻文艺的本质在于它更希望借助构想未来的多重可能以达成讽喻现实的目的。它不仅是一种“幻想的科学体系”[4](P.130),还是一种“变异”了的现实主义,或者说反思式的现实主义。科幻文学不仅事关科学技术幻想、超验知识探索和生命价值塑造,还包含科幻作家对“审美乌托邦”的意识形态建构或反思。
科幻文学缘起于欧洲,20世纪中叶在英美迎来“黄金时代”,形成蔚为大观的科幻文艺思潮。中国现代科幻意识萌生于20世纪初,中间几经断层,到20世纪末产生了新的创作高峰。“自从科幻进入中国之始,这个文类已被归化,在前所未有的新颖想象之下,流动的是‘中国复兴’的宏伟情节。”[5](P.61)在科技强国的背景下,新一轮传媒革命不仅推动了科幻文艺的传播,更激发了中国作家创作科幻文学的热情,传统科幻作家刘慈欣、郝景芳斩获科幻小说最高奖“雨果奖”则刺激了中国科幻文学的集群式爆发。网络科幻小说在新世纪20年的发展尤其突出。“就文体的意义而言,网络这个媒介造就了网络科幻文学;反之,网络文学因互联网这个新媒介具备的超文本、超链接、交互叙事等媒介特征而产生了一种接近现实又与现实保持疏离的‘科幻感’。”[6](P.196)
网络科幻小说重塑了科幻文艺的叙事传统和审美范式,“网生代”作家在继承和发扬科幻传统的基础上,依托于中国文化视角和价值立场,在主题思想、创作方法和审美表达等层面都有新的突破。得益于自由开放的创作环境、丰富多样的出版形式和高效便捷的新媒介,中国网络科幻小说的成绩举世瞩目,产生大量优秀作品,涉及星际战争与政治、“太空歌剧”和宇宙社会学、“废土”与末世生存、人工智能和复杂形态智慧生命、混杂了奇幻、魔幻、玄幻、机甲、穿越等类型特征的“软科幻”等多种题材。这些作品或重塑人与自然、社会与其他生命的政治伦理关系,或尝试不同于传统科幻叙事的创作手段与文本范式,或塑造多重身体面向的“后人类叙事”模式,展现出网络科幻作家对于“科技与文艺”这一悠久人文母题的省思,构成了当代科幻文艺的“中国经验”体系。
二、“星丛式”世界图景与副本模式
“副本”又称“别本”或“抄本”,在意义上与“正本”或“主本”对标。文学副本更接近“游戏学”中的“文本中的文本”,即“正本”故事线中的“支线”或“次级文本”。“‘副本’概念缘起于暴雪公司的网游《无尽的任务(EQ)》,其‘副本’包括‘团队协作’‘独立性’及‘冒险’,它允许玩家在游戏中建立一个‘地下城’(dungeon)或‘私人区域’,玩家及团队可以在这个私人领域试炼、探索、冒险和战斗。”[7](P.152)网络科幻小说叙事所建构的环绕“正本”的众多副本形成了“星丛式”文本结构,为读者呈现出主题多样、价值多元、情感体验多维的艺术生态,拓宽了科幻文艺的创作版图,丰富了当代文学经验范式。
最早将“星丛”(constellation)概念应用于认识论和社会批判的是本雅明,“他拒绝卢卡契的整体性结构理念”,主张用“星丛”既松散又联结的存在状态来说明概念与客体间非强制性的辩证关系[8](P.69),畅想某种类似于“星座式不断变化的整体格局”。[9](P.318)阿多诺借用此概念并将“星丛”理解为一种辩证模式。作为哲学隐喻的“星丛意味着‘一群并列的、而非整合的变化元素,它们不能被归并道一个公分母、本质性的核心或第一生成原则之下’”[10](P.14-15)。“在星丛中,元素所体现的并不是它们所表达的东西,相反,它们形成了一个网络或空间,在它内部,不断发生着变化的元素是平等地处于同样地位的,且不会被归结为某个中心。”[11](P.52)“星丛”模式揭示了“混沌宇宙”的内涵,即组成某个整体的各要素之间形成既彼此关联、相互影响、和谐共生又各自具有能动、自主及动态变化特性的复杂关系。
文艺理论视域的“星丛”模式专指文学作品的复杂文本系统。网络科幻小说的世界观设定与文本结构的框架是“星丛”概念的哲学范式在文学叙事中的具象化显现。首先,在故事层面,网络科幻小说经常呈现游戏化叙事的路径,它们以多元形态的“支线”环绕“正本”但又各自拥有情节独立性的副本来构建区别于传统叙事的文本网络。商业化写作决定了网络科幻小说的文本形态,“超长篇”的叙事容量和“分层化”故事情节是其体现“星丛”结构的典范形式。网络科幻小说同其他类型网络小说一样通过“日更”形式创作,即作者每日按照三至五千字的容量将已完成的稿子上传网站,然后构思新的情节,周而复始,直至完本,这种创作模式决定了在漫长的叙述中会出现大量游离于“正本”之外的副本存在。如《小兵传奇》就在“打怪升级”的“游戏爽文”模式中创造了唐龙获得资源、装备(武力)升级、扩充地盘、星际争霸和统一宇宙等副本组成的文本网络。多副本共存的状况也引发了小说结构上的动态平衡,即作者阶段性的创作构思往往会影响到某些副本的质量,以此产生整个“星丛”网络中某些副本相对精彩,另一些则因为作者灵感枯竭或思路受阻而质量下滑甚至“断更”成为“太监文”。例如彩虹之门完成《地球纪元》前四卷后曾持续“停更”了近两年后才创作第五卷。其中第三卷《时间旅者》和“番外篇”《恒星人的反击》这两个副本最精彩,第五卷《星尘信使》则因为“爽文模式”不彰而被读者诟病。又如“星空奇遇”题材开山之作《大宇宙时代》前半部分地球末日、沙漠之星、“恶魔族”等副本的写作都极为出彩。如果认真打磨,小说原本可以为中国读者构建类似于《星际迷航记》系列那样具有史诗气质的“太空歌剧”,但终因作者遭遇创作瓶颈以及受到资本裹挟而草草完本,着实可惜。
其次,网络科幻小说人物“具身性”生命经验也不再以单一面貌呈现在同一性的时空结构中,波诡云谲的幻想叙事驱动角色跨越平行世界、畅游星辰大海、穿梭过去未来、置身“芥子须弥”甚至漫游数字空间。如《深空之下》与续作《深空之流浪舰队》都展示了“具身性”生命体验在不断涌现的副本故事线所建立的平行世界中的“塌陷”。《深空之下》描述了后人类通过“内置”智能芯片而实现“光速思考”并进阶超级文明俱乐部。他们不仅能够在多维世界中以“数据化”的形态生存,也可以将生命数据装载到某种“生化装置”的“假体”或“湿件”中,变成某种“控制生物体”(即“赛博格”)的加强版。[12](P.314)他们更“看重(信息化的)数据形式,轻视(物质性的)事实例证;认为意识/观念只是一种偶然现象;认为人的身体原来都是我们要学会操控的假体,因此,利用另外的假体来扩展或替代身体将变成了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法来安排和塑造人类,以便能够与智能机器人严丝合缝地链接起来。”[13](P.3-4)《深空之流浪舰队》则描述了后人类的进化,他们将意识数据存储于虚拟世界,以“量子态”在数字海洋中轮回、永生。为了证明人类文明进化路的艰辛,小说建构了“樱花世界”和“潮汐锁定的星球”这两个精彩副本来描述主角张远带领“NT新人类”在宇宙中探索冒险。可见,网络科幻小说通过对其内置“副本世界”的不同设定来丰富人物的生命体验和角色功能,改变传统文艺一元化的身体经验再现与叙述方式,以此提升叙事技巧和充实科幻文艺的审美内涵。
再次,网络科幻小说在传播层面也充分融合“单向、双向、多向传播与线性传播、非线性传播”等不同形式,生成了一种多节点、动态性和网络状的“星丛传播”模式。[14](P.154)“副本叙事”所产生的阅读感受与游戏经验类似,它既是小说文本通过不同副本搭建多维故事线并以此表达科幻文学对人生多元偶然性以及多层次生命体验的一种反思,也反映了新时代网络新文艺接受的新趋势,即通过不同内容载体实现文本审美价值的跨媒介、跨文化和跨学科传播。时下,网络科幻小说的受众群体不再局限于传统科幻文学的小众圈层,书本、影视、动漫、游戏、自媒体与其他衍生文艺生产场都活跃着网络科幻粉丝的身影。2019年末,蕴含科幻元素的热门IP《庆余年》的“网改剧”所引发的现象级传播和跨媒介互动就是这种趋势的典型体现。通过网络社区讨论、电子书阅读、线下出版营销、“影游互动”与动漫改编等不同于传统文艺的传播途径,网络科幻文本的再生产空间及其审美价值也因跨界传播而获得无限的“增殖”潜能。
三、“遍历性”文本路径与游牧主体
“遍历”(ergodic)是计算机程序用语,指操作指令沿着某条搜索路线依次对树(或图)中每个节点均做一次访问。“遍历算法”的运行结果是在数据空间中产生各种节点网络和“文本簇”。文艺理论视域中的“遍历”是指某种文本类型的话语系统,“其符号源于作品中并非微不足道的要素所产生的路径。遍历现象亦见于某些类型的控制论系统。这些系统是作为一种信息反馈回路而工作的机器(或人),它们将在每次被卷入时生产一种不同的语义顺序。”[15](P.68)“遍历”文本完全区别于传统文学叙事的文本路径和话语框架,网络游戏、互动戏剧、超文本和自带叙事副本的网络科幻小说都是这一理论范式在审美实践中的体现,“遍历”呈现了这类文本内部“正本”与副本、情节主线与支线、“主本”与“番外”间的交互关系,对其人物角色的动作行为、形象塑造和艺术价值生成产生能动影响。
在网络科幻小说“星丛式”文本系统中,角色成长、冒险、寻宝和战争等情节是在不同路径的副本网络中生成的。不同副本故事线对于人物形象及其情感关系的塑造亦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如此特殊的文本路径设定与人物形象刻画也必将产生新的叙事艺术与审美经验。“遍历式”文本使网络科幻小说在叙事中产生了一种新角色,即拥有德勒兹意义上的“游牧身体”[16](P.240-280)的形象。这类角色类似于网络游戏玩家控制的虚拟人物,它们以“工具人”形式存在于小说的众多副本中,参与任务,构建情节,探索小说中的各种“异世界”,“完形”故事情节的每个“节点”,进而展现小说的世界图景。“游牧身体”“在属于别人的土地之间迁徙,就像游牧民族在并非自己的写就的田野上一路盗猎过去,掠夺埃及的财富以获得自我的享受。”在此过程中,“文本于是成了文化武器,成了一片只供私人打猎的禁猎地。”[17](P.174、171)这种角色受到叙事机制的控制,他们比传统叙事的角色更具有“赋义价值”,类型也更加多样,体现为从“具身体验”向“游牧体验”的过渡。“游牧身体”的生命体验是区别于“具身体验”的新审美范式,它是一种借助媒介技术将生命意识上传、负载、寄生、同化、融合到“异己”的装置或载体而实现主体“远程操控”的生命实践。“具身体验”意味着我们无法同时身处多元时空环境,“游牧身体”则打破传统文艺身体叙述对意识、心智和思维的束缚,因为在“赛博格化”、“数字化”和远程跃迁的环境中,“游牧身体”可以“裂变”为近乎无限多的“替身”。他们的“运动不再是从一点到另一点,而是变为持久的,没有目的和终结,没有起点和终点。”[18](P.506)借助于新技术接入数据空间的虚拟身体和数字替身,“游牧身体”不仅可以同时扮演多个角色,体验多样化的人生,改变时空规则,穿梭于不同的时空环境,甚至死而复生,直至永生。[19](P.30)作为扩展人类身体经验的文学表征,网络科幻小说中的“游牧身体”是对后人类生命机能及其与现实关系潜能的“乌托邦/异托邦”隐喻。网络科幻小说的后人类“游牧身体”经验已经超越了传统文学“具身体验”的限度,从实在界进入“超空间”和虚拟世界,变成实打实的“数字化生存”和“超空间生存”,后人类身体的塑造和体验也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自由维度。
网络科幻小说的“游牧身体”主体在其“遍历性”叙事空间、艺术创造与身体实践的表征过程体现为三种类型。一是主体在游戏世界中的“数字替身”与赛博空间NPC角色的交互对话,如升级打怪、寻宝冒险与时空穿越等。这种“游牧经验”让小说中的人物通过肉身、能量、信息流与数据等多种存在形态来获得主体性认知,如《重生之超级战舰》中肉身被毁而栖身星舰主脑的萧宇,当他进化成为“神级文明”后不仅重获肉身,而且逆转时空,让毁灭的地球重现;《深空之下》中于易峰率领“新人类”阻击被“数字病毒”控制的“阿米巴派系”外星人时利用“诺亚文明”的高维空间碎片指挥“数据战士”同“数字病毒”战斗,实现了肉身主体的“数字化生存”;《千年回溯》中陈锋在睡梦中穿越屡经剧变的未来和现在,以此搅动时空秩序、实现人类命运变革,等等。二是“游牧身体”在未来世界的奇异旅程,如星际战争、星空奇遇与异界漫游等。在《文明》《寻找人类》《宇宙的边缘世界》等作品中,高度发达的星际穿越、跃迁技术彻底解放了后人类的身体机能,使其借助不可思议的科学手段达成冲出太阳系,穿梭不同维度的时空乃至征服星海的宏图伟愿。三是后人类借助技术改造实现社会分化,或因植入智能辅助芯片而提升理性与智能变成“超人类”。智能辅助、芯片接口、生化克隆甚至“意识上传”等技术推动《大宇宙时代》《银河之舟》《云氏猜想》等标志性作品的后人类借助“思维加速”突破科技瓶颈、充实“科技树”,或以统一意识共存于多元躯体中,或作为“生命数据终端”在多维空间中共现,后人类的美好愿景最终落脚于技术狂想的艺术表征中。
网络科幻小说的“游牧身体”揭示了“后人类”近乎无限的生命机能与身体经验的多重可能。它不仅是人类身体的技术延伸,也是多姿多彩的生命活力在可然与或然相统一的生存空间的无限延宕,即身体主体性建构永远处于未完成状态。网络科幻小说建构的各类“游牧身体”让每一具身体都能衍生出无限多的“分身”或“子体”,一种生命可以体验无数种身体经验。它让生命体验不再局限物理—生理—心理机理共同决定的面目、结构和功效,获得可以自由形塑、赋义和创构生成丰富多样生命体验、生活形态和生存状况的潜力,单一有限的人生体验在语义表征中被注入了无限之“多”的审美价值追求。
网络科幻小说的“游牧身体”也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元身体”(meta-body)。“元身体”的描述来自现代科幻小说鼻祖《弗兰肯斯坦》。在其中我们不仅看到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身体标记,而且还有怪物身体意图突破主体束缚走向生命自觉的努力,肉身化的身体彻底异变为“游牧身体”,显现出“游牧式主体”对人类身体机能的“自反式构建”。作为“自反性身体”或“元身体”的后人类,其所指向的最终目的地是对制造怪物身体的人类主体的映射、操纵、质疑、反叛,乃至毁灭。《弗兰肯斯坦》中的怪物及其表现出来的“游牧主体”特性与网络科幻小说塑造的“新怪物”——外星人、人类异化/异能者、机器人、基因突变的类智人等智慧生命——几乎如出一辙。传统科幻文艺中人类对那些自己制造出来或遭遇的后人类的排斥、惧怕、厌恶以及不惜代价的虐待或毁灭行径的背后,反映了人类对生命有限性和肉身脆弱性的心理悖论:人类还没有达到上帝或神的层次,却偶然地掌握了神祇创世和造物的能力,这能力既是双刃剑也是潘多拉魔盒,人类对这种力量充满忌惮和恐惧。创世造物带来的不是成就感和虚荣心,而是无休止的心灵恐惧与精神煎熬。网络科幻小说也不例外,特别是“游牧式主体”远超人类能力的“想象性未来”,如《文明》中穿梭多维宇宙的沙星文明、《寻找人类》中突破维度和时空的“三智者”、《云氏猜想》中在四维“视界”中观看未来的云Sir、《天阿降临》中在概率空间跃迁的安琪……后人类的“游牧身体”几乎无所不能,它们全面突破了时间、空间、精神、心灵与现实藩篱的羁绊,实现了“生命意志”的大自由,这些都会让惴惴不安地迎接“后人类纪”的“旧人类”感到绝望和不甘。后人类主体“那(些)身体不能被任何人类的身体所触及;它(们)显然是坚不可摧的,只有当怪物决定把自己烧掉,它才可能被消灭。”因此,网络科幻小说中“玛丽?雪莱的怪物依然在那里游荡。它已经在我们的想像中占据了一个永久的位置。”[20](P.266)“游牧身体”在揭示叙述者的奇思妙想的同时,显然也包含着透入骨髓的警世与批判意味。
四、“反人类中心主义”的“后人类”生命政治
福柯首先使用“生命政治”来“表明一种始于18世纪的行为,它意图将健康、出生率、人口、寿命、种族等问题合理化。”“到今天,它们已经构成了诸如政治和经济问题。”[21](P.7)生命政治包括绝对权力宰制下的生命管制和社会规训统摄下的生命治理,前者标明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生命权利的绝对控制,它通过暴力机器和生杀予夺的铁血手段维系;后者则是统治者借助制度规范、法律条文和治理术等相对温和的方式驯服与同化被统治者,其中包含了伦理、族裔、媒介与文化认同的合法化,即将“生命、生活和生存问题”纳入权力/政治的规训游戏中,把这些涉及人类社会关系和生命治理的经验法理化,进而使之符合某种统治原则。阿甘本将福柯的“规训式”生命政治解码为“人的自然生命越来越被纳入到权力的诸种机制和算计之中”[22](P.163),即人的生命、生活、生存及其形而上意义的精神-哲学实践都要受到权力/技术的话语、关系和逻辑的理论建构机制的影响。罗斯对人类三个多世纪的生命政治实践有更细致的划分,他认为18-19世纪生命政治是一种事关生命支配权、族群治理模式的“健康政治”,体现了君主对被统治者的“权力意志”;20世纪生命政治更关注民族国家治理的规范化与体制化,强调柔性的规章制度、组织关系和文化习俗对人的生命意志的控制、规训与重塑,因此是一种“种族治理”和“权力规训”。21世纪生命政治则是福柯和阿甘本之外的“第三种政治”,它关注人类通过技术手段探寻生命机能与潜力,改善生命的生存条件并借此处理与其他智慧物种的关系,因此是一种“跨/泛智慧”物种的“后人类”生命“伦理政治”。[23](P.3)
早先的生命政治实践在三百年来的科幻文艺中都依托于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叙事伦理而被建构起来,但是“后人类主义”及其话语范式在1970年代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种状况。[24](P.48)后人类时代,信息、媒介和基因等“技术成为人类自身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进入到人类身体内部,影响、支配甚至控制了人类思维与生存模式。”[25](P.29)在此背景下,科幻文艺对“后人类境况”的书写总是充满批判的力量和话语的张力。以布拉伊多蒂为代表的批判后人类主义者认为,“后人类状况不是一系列看似无限而又专断的前缀词的罗列,而是提出一种思维方式的质变,思考关于我们自己是谁、我们的政治体制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与地球上其他生物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的共同参照系的基本单元应该是什么,从而引进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26](P.2)她认为“后人类主义”是对人文主义和各种人的形象的哲学批判,这一“人”的形象曾是普罗泰戈拉的万物之尺度、笛卡尔式的主体或者是人类掌控的能动性与理性的自由主体。该批判宣称要“重思”人类并在一个更大的星球生命图景中提供人类与非人类(从动物到对象与机器)的相互联系。[27](P.18)因此,在网络科幻小说中叙述者需要重塑后人类生命政治的内涵并在“人类中心主义”论调濒临破产的前提下思考其叙事伦理。对此,《废土》《间客》《吞噬星空》《狩魔手记》《死在火星上》《异人行》等网络科幻作品中的生命政治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进路。
《废土》《狩魔手记》《异人行》不约而同地描述“核战末日”后受到辐射环境改造的后人类(“寄生士”、外星基因改造人、“蝼蚁人”)与人类之间的复杂关系,猜忌、争斗、奴役、臣服与背叛构成了新旧人类间除了生存挣扎之外最重要的生命政治实践,自觉的人性拷问和“命运共同体”的忧思使这些作品被打上了审美现代性烙印。《间客》《吞噬星空》《死在火星上》则把新旧人类间的生命伦理关系放之于浩瀚宇宙的视域中,不管这些新人类(基因改良者、超强炼体者、赛博格)是在新的生态环境下自然进化的智慧生命还是按照人类意志通过基因编辑创造的异形异类,它们都会挑战人类的伦理关系,新生命伦理与生命政治也将在小说的叙事正义中得到体现。如果人类依然把康德所尊崇的“道德律令”作为身份认同的圭臬的话,那么,当我们面对克隆复制、基因编辑或人工智能介入生命实践的后人类语境时就会面临认知困惑乃至绝境。这正如《格列佛游记》这部古典后人类作品对“慧骃国”类智人“耶胡”(Yahoos)的描述:在失去了道德法律和人性约束的“废土末世”,人变成“非人”,他们“例释了人性在丧失理智或其他约束时所表现出来的某些极端层面——暴食、纵欲、贪婪、狂躁、嫉妒”而又暴力、龌龊和淫荡的生物学特征[28](P.118),在极端生命政治语境下,“兽性的复生”与“人的兽性化”的“二律背反”构成了网络科幻小说叙事伦理的内驱力。
科幻文艺“后人类叙事”的伦理困惑与道德悖论的根源也许仍然在人类自己身上,网络科幻小说的相关思考和传统科幻文艺对于“技术生命”以及人类变成“伪神”后的伦理焦虑一脉相承,“弗兰肯斯坦”的幽灵仍然在人类头顶上回荡。此外,人类对自我主体中某些“神性”要素依然怀有深刻的警惕和忌惮。“也许,我们将站在人类与‘后人类’历史的这一巨大分水岭的另一边,但我们却没有意识到分水岭业已形成。”[29](P.101)“后人类叙事”对“人的问题”的审视——人权、人性、意志和尊严的异化,技术扭曲人性、人心——彻底改变了我们对生命政治思考的视角。随着生物医学、基因工程、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科技已经成为人类生命实践的延伸,“人类逐渐‘非人’化,福柯预言的‘人的被抹除’可能即将发生”,在“后人类叙事”伦理构建的网络科幻小说中“人类并不享有保存自身生物特性和身份的特权,人类被抹除的可能性并不意味着叫停科技的必要性,人类的‘非人’化是一个正在发生且无须哀悼的事实。”[30](P.126)这也是我们反思后人类所带来的伦理冲击的目的所在。
网络科幻小说的“后人类叙事”本质上为读者精心地创建了一种“二律背反”的“乌托邦/异托邦”系统。后人类生命政治的审美建构“不仅仅属于作家的个人创造,而是反映出特定历史时期人们理解世界和想象未来的方式,以及孕育这种创作范式的社会与文化实践”[31](P.21),作为叙述手段和构思方式,“这种方法投射了一种世界,这个世界其实是与我们现实世界生存情境息息相关的,但是在这个世界里,所有的情境似乎都更等而下之。”[32]这种“乌托邦/异托邦”系统在审美层面为读者营造了一种比现实更加黑暗、无序、非理性与不可见的“后人类境况”。在《小兵传奇》《庆余年》《希灵帝国》《修真四万年》《宿主》等作品中,这种畸形的社会形态更是人类社会所有旧制度的“返祖”:皇权帝制、家族独裁与严刑峻法的奴隶制度堂皇地并存于未来“哥特社会”的暗黑狂想中。因此,网络科幻小说的生命政治是对理想社会的“反建构”,它基于人类伦理关系的善—恶、好—坏、美—丑、文明—野蛮等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设想乌托邦社会形成后包含其中的“反结构”“反体制”“反潮流”和“反人类”等范式,即理想社会中仍然存在着未知的假恶丑和“非人化”现象,它们仍然是人性自我完善的死敌,它们消解了人之为人的情感、思想、自由和道德标准,使人在后人类语境中异化为“非人”,或作为现实生活的“想象的能指”而存在。“乌托邦/异托邦”的想象编码与审美范式之所以受到网络科幻小说的欢迎,是因为它们在“乌托邦空想开垦过的土地上劳作,也就是试图构想一种与此截然不同的日常生活,没有竞争或忧虑,没有异化劳动和对他人及其特权的羡慕和嫉妒”[33](P.79),更没有人性向兽性的堕落。网络科幻小说的“后人类叙事”在新媒体时代构建了新的话语机制与理论维度,即针对“人类纪”普遍存在的“人类中心主义”伦理陷阱和生命政治危机而提出一种新的反思策略,同时它也揭示了中国网络科幻小说“后人类叙事”的“乌托邦/异托邦”话语变奏内在的复杂语义逻辑,并在和平崛起与民族复兴的新时代语境下重塑文学生命政治想象与伦理实践的美学空间。
五、结语
网络科幻小说的后人类生命想象及其所构建的生命伦理观与生命政治学,是审美实践对现实社会治理模式与组织规范体系的一种“虚构性预演”或“想象性建构”。这种“建构”与“预演”既能够为当代人类提供预见现实社会生命政治及其治理机制在未来时空维度中的发展趋势和直接影响的机遇,也通过文艺审美意识形态话语的能动力量对现实生命实践的组织制度、运作机制、治理体系和价值规范提供了必要的警示、讽喻和反思的可能性。网络科幻小说借助于这种建基于科技与人性、生命与政治、审美与社会等维度之上的冷静思考与批判,充分地发挥了科幻文学以“技术狂想”、“后人类叙事”和审美新范式来反映、干预和改造人类自身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此承载“科幻现实主义”的叙事正义与美学伦理,揭示出符合时代特色的审美价值观与方法论,构建科幻文艺生命政治学的理论话语规范体系。
参考文献:
[1]赵泠.科幻文学的重要性是什么?[EB/OL].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84569010/answer/1124121560,2020—04—13/2021—04—18.
[2]陈楸帆.有生之年,每个写作者也许都将与AI狭路相逢
[N].文汇报,2019—03—21.
[3]达科?苏恩文.科幻小说变形记:科幻小说的诗学和文学类型史[M].丁素萍,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
[4]王峰.叙事与奇迹:科幻文本中的人工智能[J].南京社会科学,2018,(8).
[5]宋明炜.中国科幻新浪潮:历史?诗学?文本[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
[6]钟舒.赛博空间:中国科幻文学的一个批评语境[J].当代文坛,2020,(6).
[7]鲍远福.网络游戏与新媒体时代的文艺理论[J].内蒙古社会科学,2019,(6).
[8]张晖.隐匿于块茎星丛中的区块链美学[J].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0,(5).
[9]斯蒂芬?布隆纳.修复碎片:沃尔特?本雅明的救世唯物主义[A].朱宁嘉,译.刘纲纪.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7辑)[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0]
Martin
Jay.
Marxism
and
Totality:The
Adventures
of
a
Concept
from
Lukács
to
Habermas[M].Berkeley,1984.
[11]吴静.德勒兹的“块茎”与阿多诺的“星丛”概念之比较[J].南京社会科学,2012,(2).
[12]唐娜?哈拉维.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M].陈静,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
[13]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
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M].刘宇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14]何志钧、孙恒存.数字化潮流与文艺美学的范式变更[J].中州学刊,2018
,(2).
[15]黄鸣奋.超文本美学巡礼[J].文艺理论研究,2002,(2).
[16]吉尔?德勒兹、费利克斯?瓜塔里.游牧思想——吉尔?德勒兹
费利克斯?瓜塔里读本[M].陈永国,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
[17]
De
Certeau,
Michel.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M].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18]德勒兹、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M].姜宇辉,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
[19]邓淑贞.后现代视阈下的角色扮演[D].西南大学硕士论文,2011.
[20]彼得?布鲁克斯.身体活:现代叙述中的欲望对象[M].朱生坚,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21]米歇尔?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A].汪民安,译.汪民安、郭晓彦.生命政治:福柯、阿甘本与埃斯波西托?生产(第7辑)[C].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22]吉奥乔?阿甘本.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M].吴冠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
[23]尼古拉斯?罗斯.生命本身的政治:21世纪的生物医学、权力和主体性(导言)[M].尹晶,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24]颜桂堤.后人类主义、现代技术与人文科学的未来[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12).
[25]王影君.后人类时代的种群危机——阿特伍德异乌托邦三部曲的生态女性主义研究[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
[26]罗西?布拉伊多蒂.后人类[M].宋根成,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
[27]左尔坦?西蒙.批判的后人类主义与技术后人类:两种后人类未来的文化讨论[J].社会科学战线,2020,(8).
[28]罗伯特?斯科尔斯、詹姆斯?费伦、罗伯特?凯洛格.叙事的本质[M].于雷,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
[29]弗朗西斯?福山.我们后人类的未来:生物科技革命的后果[M].黄立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30]徐璐.幽灵游荡:日本科幻动漫中的核威胁[J].文艺理论与批评,2020,(6).
[31]王瑶.从“小太阳”到“中国太阳”——当代中国科幻中的乌托邦时空体[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4).
[32]王德威.乌托邦,恶托邦,异托邦——从鲁迅到刘慈欣(之一)[N].文艺报,2011—05—17.
[33]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未来考古学:乌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说[M].吴静,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