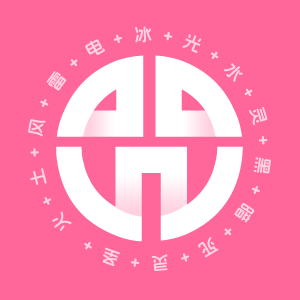“网络即文学”:一种敞开的历史
就顺着“打包”说吧,物品被打包后,总需要列一份清单,写清其性状、功用、来龙去脉,这对细致的打包者而言,又有一次重新命名、研究的契机了。一些历史问题终于被重新打开,而网络文学的历史中,最大的一个问题便是:现在的“网络文学”似乎成了网络类型小说的专称,但在文学刚刚触网时,“网络文学”指代的是所有创作、发布在网络的文字——小说、诗歌、散文诸体兼备。这样的转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要给打包好的历史寻找确定性的解释,并非难事,从结果追溯、建构,总能在时间的尘埃里找到一张适合的封条。但如果面对一个肆意敞开、不断翻新的包裹呢?哪一张标签恐怕都是不合适的,它需要一种敞开的历史。敞开的历史,就是要反复分辨事物中的偶然、缝隙与消逝的可能性,如此才能让人更清楚它所具备的潜能——这也是其走向未来的资源。中国网络文学的发展史,难免要被描述为一种新文学形态的成长史。但网络文学的发生,不仅是一个建构性的文学史事件,也是一个解构性的理论事件,它在推动文学格局发生变化的同时,显然也开启了人们对文学观念追索、检视的过程。
在封存的网络文学史中,人们讨论网络文学,往往会在“网络”与“文学”两个支点上做文章,辨析是谁包含谁,谁影响谁。这些立论都有其价值,但如果不是把这两个事物理解为解题的“支点”,而是视为两种可以互相激活的“视点”,就会意识到,“网络”与“文学”的内部实际是高度相通的。链接一切,消除远近、高下之别,让人更好地看到、参与世界,这是“网络”带来的最重要礼物。那么,“文学”呢?马克思·韦伯说,“人是悬在由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笼而统之的“文学”,便是一张由无数人编织的“意义之网”,它是弱者的伟业,要在寻常中发掘精微,在废墟之上升腾希望之火,要不断发现创造,化腐朽为神奇,它必然需要无限联系,无限交流。更透彻的定义是,“文学是一种奇怪的建制”,是“自己之外的一切事物”,无处不在而又空无一物——这不就是今日之“网络”?
在互联网发展初期,人类对它所包含的变革可能展开了无数畅想,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数字化生存》一书。但这些看起来极其丰富可感的“生存图景”,对于初生的互联网而言,意义仅在于动员与召唤。与其说是互联网带来了新的世界,不如说它打开了一扇窗户,去鼓舞人们想象世界。对更美更善的事物的想象,几乎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当每一个技术窗口出现,这些想象都会被召唤出来,求得落实的可能。在文学历史中,这些想象被一代一代人付诸笔端,便构造了所谓的“文学母题”。而此刻的“网络”,毫无疑问,正是人们以自由之名召唤出的一种母题:创造一个新世界!
这个新世界中当然包含了新文学。互联网的出现,让人们对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充满期待,这突出体现在对网络写作“自由无功利”这一特性的指认上。2000年,李洁非在《Free与网络写作》里将“free”作为网络文化精神,认为这个英文词包含的“自由的”“自主的”“打闹的”“免费的”等义项,都是网络文化的特征。然而一年后,在榕树下网站担任内容总监的先锋小说家陈村就感慨“网络文学的最好时期已经过去了”,因为“它的自由,它的随意,它的不功利,已经被污染了”。
自由、无功利,只是一种畅想。从生产机制的角度,网络文学迄今二十余年的发展方式,可以被归纳为“榕树下模式”与“起点模式”。“榕树下模式”以榕树下网站的制度为代表,采用编辑审核制,以纸质出版为主要盈利方式,内容多样,尤其鼓励诗歌散文作品,堪称文学青年的抒情写作;“起点模式”以起点中文网的VIP在线付费阅读制度为核心,内容以类型小说为主,实为普罗大众的故事消费。
两种生产机制的背后是两种文类,两种关于文学审美的体认方式。文学青年的自由抒情,是碎片化、随机性的,是以抒情、漫游为主的审美现代性,本就建立在对工业现代性的批判的基础上。其商业上的失败,是对文化工业的本能拒斥,这是抒情现代性的宿命。网络文学青年的写作,缺乏持续的读者以支撑起一个有效的文学生产循环体系,在失去轰动效应之后,逐渐淡出了网络。
类型小说针对人的欲求差异对小说进行分门别类,类型规则相对明晰,方便指导当时的小说创作。网络类型小说是满足大众消费诉求的文学形态。其创作方式是可以进行商业化培育、引导的文化工业生产方式。网络类型小说的连载继承了纸质期刊出版的连载形式,同时利用网络技术带来的阅读交流便捷性,使作品的交互性、陪伴感大大加强。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类型小说读者所进行的只是故事层面的消费,并不限定于文字形式。在技术手段成熟之后,他们的“故事需求”,可能就会转向视频、游戏等形式。
“榕树下模式”和“起点模式”实际上代表了“网络”对于“文学”的两种解放抑或塑造路径:榕树下创始人朱威廉宣扬的“要让普通人也拿起笔来”,旨在鼓励普通人自由发表、随意讨论文学作品。这是创作与交流环节的解放,注重的是想象与表达的过程,而不是写作的成果是否符合某种文学规范。互联网让无数的网友成为有无穷创造潜能的作者,他们的发言,当然包括文字、图像、表情符号等等,都是一种个人的创造。依照此前的审美标准,这些作品或许是粗制滥造的,还有一些是拙劣的模仿,毫无新意可言。但对于个体而言,如果这是他们能够找到的最好的表达方式,他们的创造就是“艺术”。从这个角度看,网络文学的意义就不在于创造多少传统文学标准下的“经典作品”,而在于吸引了多少普通人参与了这场文学实践。
在“起点模式”下,起点中文网创始人吴文辉所说的“网络文学恢复了大众的阅读梦和写作梦”,强调的是网络降低了类型小说的生产、传播和阅读的成本,促进了小说创作的规模化,满足了大众的类型故事消费欲望。他之“大众”,是现代消费者,而非抒情漫游者。商业的成功,使得“起点模式”大行其道,网络文学的文类有了显著的收缩,从小说、散文、诗歌多种文体交相辉映,变为长篇类型小说一体独大。
网络中的“文学青年”写作再难恢复榕树下网站的盛况,但后来的豆瓣阅读、“ONE·一个”等平台的探索可以看作文学青年写作的延续,它们仍在顽强地探索,保留着网络文学在长篇类型小说之外的可能性。在“榕树下模式”“起点模式”之外,还有“新小说”“黑蓝”等纯文学网站论坛,这些作者可以说是“纯文学”的预备军,他们在网络中交流、学习,未形成独立的生产机制,但始终坚持着先锋探索。新小说论坛已经关闭,曾活跃其上的徐则臣、盛可以、曹寇、李修文、艾伟、张楚、朱山坡等人,现在已成为“70后文学”的中坚人物。他们那些自由探索的精神,到底是网络空间赋予的,还是文学本身的,已没有必要分辨。网络即文学,文学即网络。
事实上,在网络类型小说里也形成了猫腻、烽火戏诸侯等“文青作家”,他们的作品在类型小说规则下,注重文学性和思想性,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当年文学青年写作的另一种殊途同归的深化。类型小说还在不断吸收元素,融化新的文学资源。
文学青年的网络写作虽然在商业中宣告失败,但他们对自由书写与阅读的热切向往,对世界的关注与真诚思考,并没有彻底消逝。他们在短暂、飞逝的时间之网里,留下了恒久的感动,创造了属于自我的意义。这些都是网络文学的遗产,作为“幽灵”存在于网络空间,随着网络写作实践的展开,会被不断召唤、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