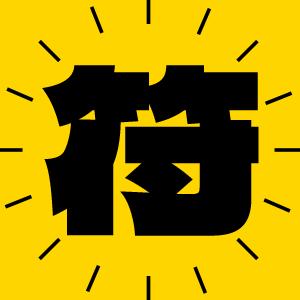人生隐宿命通俗见人性
网络作家猫腻创作的《庆余年》是一部古装权谋长篇小说,共计七卷,讲述了一个拥有现代思想的穿越少年范闲的传奇故事,他自小在养父、师父的着意培养下文武兼备,在一系列阴谋中历经家族、江湖、朝堂的种种考验和锤炼而声名鹊起。该小说囊括了穿越、权谋、悬疑、爱情、亲情、友情等多种题材和元素,讲述了政权与政权、家族与家族、帝王与臣子、臣子与臣子、权贵与平民、父与子、嫡与庶之间的斗争,既有朝堂上的暗流涌动,也有伦理间的扑朔迷离,几乎具备了通俗、娱乐作品的一切要求,以煽情离奇的情节直接诉诸观众情绪,表现了生离死别等世俗化的人情世故,憧憬了一种理想状态下的社会生活,妙的是在富有英雄主义和浪漫色彩之余又能关照现实,是传统道德和成长故事的现代版,作者通过其作品表现出东、西方传统文化对现实生活的诠释和新解。
简单地说,该小说的创作技法可以概括为“以故为新”或“化古为新”。这句话其实是世人对“江西诗派”创作方法的概述,江西诗派的开山祖师黄庭坚曾说过:“古之能为文章者,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所谓“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就是指借鉴前人的“陈言”和套路,化用到现实生活和场景中来推陈出新,叙说自己的主题内涵。《庆余年》的创作方法与此相类,在情节、结构、形式和人物设置上古今合璧,巧妙地借鉴了好莱坞的情节剧、传统剧作、古典小说(如《红楼梦》)以及神话传说等,“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多处埋伏笔、设伏线,剧情充满反转和起伏,节奏明快。全剧以人文关怀为底蕴、以劝善济世为主题,充满了对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崇敬之意。
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曾对好莱坞情节模式有过精辟的概括:“一般来说,是主人公不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失去了对生活的控制,然后设法以某种方式重新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这话应用到男主角范闲的身上也恰如其分。范闲的存在重现了柏拉图经典的哲学三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前世体弱多病的范闲在穿越后经历了身份错位的迷惘后,开启了一番思想观念上的转变,先前只是打算“好好活着”,但是后来遭遇阴谋暗算,护卫受牵连牺牲,于是他奋起反抗,尔后身不由己卷入朝堂争斗,最终想要“改变规则,重塑天地”,以一己之力,与世界为敌——其实就是与摆布自身命运的势力以及固化的规则和制度为敌——而这也是其母叶轻眉曾经的壮举和誓愿。
因为穿越后再世为人,所以范闲对于生命格外珍惜和敬畏(无论是自己的还是朋友、下属的),充满着一个生命个体对于自身生命的清醒认识,包括生存、安全和死亡意识等,潜意识里避忌伤害和死亡。但在京都步步为营的环境下,范闲逐渐与过去那个看似“贪生怕死”的自己挥剑断别。在其他人眼里死的不过是几个“护卫”,而对于范闲而言却是三条宝贵性命的无情流逝,于是对于生命的痛惜之情以及对他人生命负责的责任意识刺激到范闲去以杀止杀、以武止戈,拼死当众击杀了仇人,这失常的举措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生命意识的体现,“你身边的人都是因为你自己聚拢起来,如果你想操控他们的人生,就必须保护他们的人生,所以这些护卫的生死是你的责任”。范闲强烈的生命意识不仅只针对自身和至交、亲人,甚至还体现在对待敌国暗探的态度上:在鉴查院的牢狱中对司理理用刑,也不过是为了间接给她一条活路,借用陈萍萍的评语就是“心温柔手段狠”,这都源于他内心深处对他人生命的尊重。
除却浓烈的生命意识和平民意识的体现,该小说还流露出浓郁的人文精神,表现为对人性、价值、命运的描摹和追求。作者尤其擅长在江山伟业的大冲突中用小细节去描绘人物,刻画人物角色的人性以及人最基本的欲望和情感,凭借真挚动人的情感细节,带给观众深深的感动。这些感动都来源于一种对于人性、情感的深层次共鸣,读者借以感受到残酷现实背后的理想主义和人文情怀。小说中的那些主角、配角、反派乃至路人都是鲜活真实的人,人物性格饱满。在作者笔下,他们以不同的方式热爱着这个世界,以不同的方式追求着他们想要的生活,他们都努力地生活着,或为儿孙、或为家族、或为梦想、或为信仰。那些简单而朴素的尊严与情感是最朴质无华却又最打动人心的心灵震撼。譬如范闲的奶奶,身为皇上的奶妈却身居僻境,表面上对范闲不闻不问听之任之,实则是在以自己的方式督促和锤炼孙儿早日成长,羽翼渐丰,爱之深望之切。旁人皆以为范闲是庶出而不受待见,但聪颖的范闲与奶奶有着彼此的默契,祖孙俩互相扶持。但在离别澹州前往京都时,少年持重的范闲难得失态,用一个非常现代的告别方式向奶奶道别:“将老太太狠狠地抱在怀里,用力地在奶奶满是皱纹的额头上亲了一大口。”动作虽简单,情感却复杂:因为他深知,此一去未必能回,那些未说出口的眷恋与感慨便藉由这一个动作传达出来,分外动情。又如开始时扮演反面角色的柳姨娘,作者同样不吝笔墨,展现其善意、人性的一面:她是一个有着真实欲望的世家女性,颇有心计,但是其子范思哲资质平庸,与范闲相比有如云泥之别,她纵然心有不甘却又不得不收敛性情,于是她的心情总在嫉恨范闲优秀与气愤范思哲不争气之间来回摇摆,有的时候甚至为了范家而护佑范闲,因为在外敌入侵时他们却又是亲人阵线,保持着微妙的、表面的和谐,这是时势所造,也是人性所在。
此外,该小说的创作技法还涉及了一个东方式的“寻母情结”和西方式的“弑父情结”的融合。小说中的“寻母”和“弑父”是有时间上的先后顺序以及逻辑关系的,以寻母始,以弑父终。因为寻母得知母亲被杀的真相,于是最终杀死父亲为母报仇。剧中的弑父情结并非俄狄浦斯式的无意为之,而是在知情人的引导下寻找自己、寻找真相的过程中了解到实情,于是最终才决定去抗衡、弑父。寻母是寻找根源,而弑父则是推翻权威、开创未来,二者的融合可以算作是东西方思想文化的一种完美结合。范闲的“寻母情结”是回归根源,继承遗志;而他的“弑父情结”是双重意义上的,既是身体物质上的谋杀,也是自我主导权和社会主动权的褫夺。
该小说虽是一部权谋作品,但因为作者铺设了大量的伏笔和呼应,导致情节曲折多变,常常出人意料,因而也就同时具备了悬疑小说的色彩。小说中设置了一个推进情节向最终真相发展的功能性人物和场所——叶轻眉和神殿——是小说中一个有待于给出答案的公开秘密,也就是小说精心设置的“麦格芬”。麦格芬手法是由希区柯克提出并惯用的电影技术方法和表现形式,即设置一个观众预先得知的关键物事,是情节发展的重要线索,是人物角色对话、行动甚至整个故事的核心,时时刻刻引导剧情,吸引观众。小说始终围绕着神秘的但不可接触的神殿和来自神殿的叶轻眉而展开暗线情节,小说便是围绕着这个既定的“麦格芬”,不断引出矛盾又消除矛盾,去迎合或超越观众的期待,催生出生物性的轻松快意。
与同类题材相比,《庆余年》堪称是一部情节复杂、格局远大的古代传奇,它一直传递的都是“平等”的理念,不管是穿越而去的现代人范闲,还是终生隐忍布局的陈萍萍,他们捍卫的都是一种平等、自由、不畏强权的信仰以及对理想主义的无限追崇,包括对事业、爱情和友情的无限忠诚。比如叶轻眉,叶轻眉其实可算是小说中的隐形女主,虽然出场仅仅几个片段,却光彩照人,是让男性包括庆帝、范建、陈萍萍、五竹、四大宗师等人终生仰望和怀恋的精神向导。叶轻眉就是一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她希望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大同社会,百姓皆遵法知礼,同情弱小,痛恨不平,“我希望庆国的人民都能成为不羁之民。受到他人虐待时有不屈服之心,受到灾恶侵袭时有不受挫折之心;若有不正之事时,以修正之心战胜恐惧;不向豺虎献媚……”又比如陈萍萍,陈萍萍也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不同于叶轻眉,他的理想主义不是生民安泰,也不是王朝的万古长存,而是牢牢守住心中那个女神熠熠发光的理想。守护他人的理想一生,这何尝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理想主义?陈萍萍外冷内热,黑暗阴郁,又足够忠诚。他对叶轻眉的虔诚度,绝对是超过对自己生命的重视度。他用毕生时间和精力布下了一盘棋,一方面引导范闲成长、为范闲铺路,另一方面试图以己之力抗衡庆国之主,重建新秩序。他是终生追求信仰并至死无悔的无名强者。
稍稍令人可惜的是,尽管《庆余年》架空了历史、颠覆了历史,是一部充满现代思想和意识的穿越剧,但同时也是一部充满“杰克苏”男主光环的升级爽文。它因为过度追求生理上的爽感,比如小说中大部分的年轻女性都寄情于男主角等设置,导致情节走向和人物性格的塑造上求全求满,反而变得失真矫情。男主角范闲的出生与成长宛如一场“楚门的世界”,被人控制和监察,是一位现代思想与传统身世、制度碰撞的矛盾体,在历经重重考验与磨炼之后,他对于人生和命运的理解和思考应该是深刻而不俗的,但是因为编剧所赋予的“主角光环”,范闲一旦遇难,必有救兵,这便给观众带来错觉——他遭遇到的所有阻力,都被他的“好命”消弭。原本层层铺垫的戏剧冲突,也就在一瞬间泄了劲。那些主角在困境中应当经历的磨砺也随之消失。看似命运坎坷,但是实际上观众根本没有深层体会到主角面对困难和未知的无力无奈感与突破困境的畅快淋漓感,有的只是“命真好”的喟叹和歆羡。于是乎,这种对于人生、命运的思考深度和力度顿时被削弱了许多。
实际上,刨开外挂的主角光环,男主角范闲的身世命运其实充满了矛盾和悲剧,是一个披着所谓幸运外衣的注定悲剧者。他拥有现代思想,独立自主,向往平等自由,但小说中其他人偏偏都对他有所图或有所求,希望他按照他们的冀望或是设定的路线和轨迹前行,但男主不愿意,这便形成了控制与反控制、抗争与反抗争的矛盾。故事最后的悲剧性因素在于命运的不可抗性,兜兜转转,范闲还是走上了一开始就被规划好的结局。看似是男主自愿选择的路线,但其实质还是在按照陈萍萍等人的布局进行着,最终走向与亲生父亲生死相对的结局。这便是最大的悲剧。真正的悲剧不是绝对的正与绝对的邪的交锋而后正义的一方失败收场,不是一方完全占理而另一方完全理亏而后占理的一方失败收场。借用黑格尔的悲剧理论就是,悲剧的实质是伦理的自我分裂与重新和解,伦理实体的分裂是悲剧冲突产生的根源。范闲的悲剧性起源即是如此:生育他的人,也是遗弃他的人;而成就他的人,也是摧毁他的人。他始终处在两难的抉择中,被迫自我分裂与和解,桎梏着无法走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