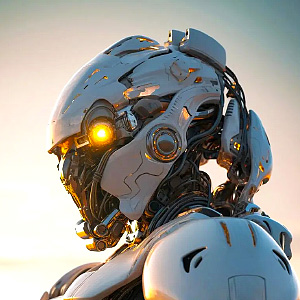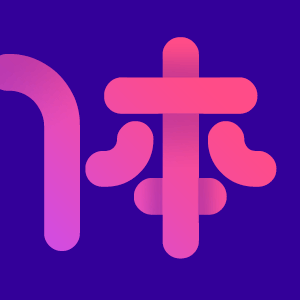从武侠的“民族”到网文的“天下”
虽然网络文学在很多时候以架空世界为背景,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的空间构造不具备现实性。相较于上个世纪武侠世界的辽汉之争、夷夏之辨,新世纪兴起的玄幻网络文学则更多地诉诸四方融合的“天下观”。当武侠小说以民族家国作为渲染正统和悲情的主要元素时,玄幻网文已经不再纠结于上述问题,多元共生成为诸多玄幻武侠先验的世界观,并由此决定了它们的空间想象。
金庸的小说之所以在众多武侠小说中脱颖而出,原因之一即为金庸以民族家国的情怀将武侠小说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从郭靖、杨过式的汉族英雄(《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到萧峰式的少数民族英雄(《天龙八部》),最后到韦小宝式的“杂种”英雄(《鹿鼎记》),展现了武侠小说民族观的扩大。但是无论是从对民族优劣的比较走到对民族间地位是否平等的思考,还是将民族对抗的故事讲成民族同化、统一的故事,其中一以贯之的,是以民族家国为思考单位的世界观。
相较而言,当下商业与情怀“双赢”的网文作品,如跳舞的《恶魔法则》、猫腻的《将夜》以及天下归元的《扶摇皇后》等,在空间感上超越了传统武侠的设定。跳舞在《恶魔法则》中设定了一个立体化的多元文明世界,帝国文明与神殿文明分庭抗礼,此外还有超然独立的魔法文明、失落的大雪山文明、没落的骑士文明、落后的南洋文明,被定性为罪民文明的精灵、龙族、兽人、矮人文明,以及被抹去痕迹的魔族文明。既有海洋文明,也有游牧文明。既有神文明,也有巫文明、魔法文明。他们各有自己的生活和文化方式。猫腻在《将夜》中对世界的设置也有异曲同工之处。昊天道门为最高文明,此外还有书院、佛宗、魔宗,以及荒人文明。在国、族、部落的交织中,人们以文明为最高认同,建立起对整个世界的认知。《扶摇皇后》的五洲大陆也以不同的文化、文明作为区分五个国度的分界,并且以五洲大同的结局表达了多文明融合的理想。这些作品代表性地展现了一个多文明的世界,各个文明有不同的信仰、信念、思维方式与认知结构,他们彼此接触的过程中充满冲突与对话。民族的概念淡去,兴起的是文明的概念。民族的边界(无论有形的,还是心理的)都不复存在,代之以文明之间的对话和冲突。
从武侠的“民族”到网文的“天下”,通俗文学在空间观方面的变动,不仅取决于作家代际的更替,而且取决于整体意识形态的变动。新世纪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动,使得既有的民族主义思维方式式微,亨廷顿所谓“文明冲突”逐渐成为空间政治的重要问题。一方面,全球化使得贸易和文化交流愈加紧密和频繁,原有许多民族主义问题似乎不再成为问题;另一方面,文明的分歧和争议渗透了空间政治的方方面面,带来了新的矛盾和问题。文化归属、思想归属代替民族、种族成为身份认同的主要内容。文明认同将作为更大的文化实体,不仅超越国与国这样的政治实体,主导世界关系与多级格局,而且下沉到每一个个人,在新的空间关系中重新认识自我。《将夜》中,书楼被称为“旧书楼”,因为只有“思想才是新鲜的”,世界被认为是所有人意识的集合,人是怎样想的,世界便是怎样,反之亦然。“认同”作为文明的凝聚力,为世界区分出多文明的形态。
文明的差异、冲突以及理解通道的找寻,成为当下空间政治的重要议题。想象文明差异,思考冲突和寻求融合,正成为诸多网络文学的基本叙事动力。网文的多文明“天下”这一设定正是在回应这个问题。各执一词是由于“立场不同,道理万千”,是文明与文明的差异,造成了思想与文化认同上的诸多分歧。《恶魔法则》中,神有神的诉求,魔族有魔族的愿望,精灵族有它们的信仰,龙族有自己所以为的荣光,人类有人类的行事逻辑,他们(女神、魔王、精灵王等)由是缠斗;《将夜》中,昊天既是信徒所惧怕的冥王,也是佛宗所记载的明王。光明与黑暗、崇高与卑鄙、是与非、善与恶、正与邪都并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建立在不同的世界体系中;《扶摇皇后》五洲大陆的分崩离析,阴谋权斗,也在于价值序列的差异性。
如此设置“文明的冲突”,使得网文获得了相较于武侠更具有“对话性”的意义层次感。《恶魔法则》中人类的各个族群,人与兽,或是龙族、精灵族、兽人族等,他们各有自己的生活和文化方式。作品并非贬此褒彼,人类也好,龙族也好,或者是皇家、贵族、魔法师、武士,作品都没有将之平面化,而是写出了各自的复杂性。他们各有不同的信仰、信念、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性,彼此接触过程中相互对照。作品甚至借助由蛇化身的美杜莎来审视、反思“人性”的矛盾和问题。借精灵族王落雪的口,来反思“人类的历史,不正是一部同类之间杀戮的过程吗?不管是这个世界也好,甚至就连杜维的前世那个世界,古今中外,都是如此!”正是这些复杂性和对话性,丰富了作品的意义表达。
网文并不是“非现实的”,相反,无论其背景如何“架空”,“现实”都深入网文的表达体系,构成了网文的先验。从武侠的“民族”到网文的“天下”,网文空间观的转换所书写的正是当下新的地理政治和身份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