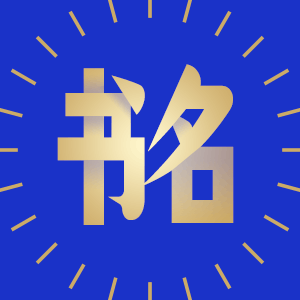中国人的年夜饭不能少了哪道菜?
导读:中国人的年夜饭不能少了哪道菜?自古至今的年夜饭谁唱主角?鱼,年年有余的鱼。“鱼图腾”的幕后,隐藏着的实则是“龙图腾”。中国人,不都自称龙的传人嘛。
中国人的年夜饭,家家户户都要烧一条鱼,供着,节日过后才吃。取“鱼”与“余”的谐音,象征着“年年有余”。这条鱼需完整,有头有尾,以表示做事要有始有终,才能功德圆满。全家人的心愿都寄托在这条鱼身上了:它已超越一般食物的概念,而成为幸福生活的标本。
辞旧迎新之际,谁不希望家有余粮、家有余钱呢?谁不希望年年如此呢?由这个细节即可看出,中国人一直是一个生活在希望中的民族。它之所以有希望,仅仅在于它从不绝望;哪怕承受着苦难或贫困,也能跟一条象征主义的鱼相濡以沫,获得心理上的安慰。这就是它的希望所需要的最小本钱。而希望本身,却构成它最大的生命力。
在几大古老文明中,似乎只有中华文明如鱼得水、年复一年地延续到今天,每一道年轮都清晰得像刻出来的。如果没有精神上的东西支撑着,很难保持这种周而复始、以不变应万变的秩序。
根据传统习俗,这条带有礼仪性质的鱼,最初用鲤鱼,后来才推而广之,用哪种鱼都可以。
为什么鲤鱼是首选?因为中国人的信仰中,鲤鱼最吉利。《神农书》里有一“排行榜”:“鲤为鱼之主。”还有人说:“鲤鱼都是龙化。”黄河鲤鱼,习性逆流而上,一旦跃过位于今山西的龙门,就摇身变成龙了。当然,此乃中国人为鱼类所臆造的最优美的一个神话。
连理智的孔子都信这个。特意将自己的儿子命名为“鲤”。能说他不是望子成龙吗?
鲤鱼在中国,堪称鱼类的“形象大使”,年画上描绘的大多是鲤鱼,增添了喜庆的气氛。我个人认为:跃跃欲试跳龙门的鲤,跟周游列国的孔子一样,可以构成古老黄河文明的图腾。所谓“狼图腾”,其实是舶来的,并非本土所有。符合中国人品性的,还是“鱼图腾”。
道家始祖庄子《逍遥游》,开篇即说“北冥有鱼,其名为鲲”,根据其描述,此种神奇的鱼比当代的航空母舰还要大得多,而且能化身为高飞九万里的鹏鸟,绝对算壮志凌云。这跟鲤鱼跳龙门的传说异曲同工,只不过更为豪放。
“鱼图腾”细化为“鲤鱼图腾”,就较接近后来占主流的儒家思想了:达则兼济天下,贫则独善其身。学而优则仕,历朝历代的科举制度,使“鲤鱼图腾”由梦想兑换为现实。龙门之上是官场。
“鱼图腾”,中国特色的“变形记”。不管老庄还是孔孟,本质上都属于精英文化。来自于大众,又时刻准备着脱离大众,转而领导大众。“鱼图腾”的幕后,隐藏着的实则是“龙图腾”。中国人,不都自称龙的传人嘛。
鲤鱼之吉祥,还在于它见证了最早的“真龙天子”,黄帝。《河图》:“黄帝游于洛,见鲤鱼长三丈,青身无鳞,赤文成字。”据说鲤鱼额头有字,是鱼中的帝王,或龙的化身:“额上有真书王字者,名‘王字鲤’。此尤通神。”(见《清异录》)
中国的神话中,能化而为龙的,除了鱼之外,还有马。马也是“龙种”,正如鲤被封为“稚龙”(婴儿期的龙)。因鲤鱼有五色,古人还拿马来相比:“赤鲤为赤骥,青鲤为青马,黑鲤为黑驹,白鲤为白骐,黄鲤为黄雉。”跳龙门的黄河鲤鱼,浑身火红,属于赤鲤,正处于“转型期”。
孔子所谓“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脍”当指生鱼片。中国人吃生鱼片(犹如今之三文鱼),很早的。切脍,越细越好,首先仍是鲤鱼。尤其宋朝,用现捞上来的黄河鲤鱼作生切鱼片,因宋太祖爱吃而流行为东京汴梁的一道名肴。
“黄河鲤鱼,是以压倒鳞族,然而到黄河边活烹而啖之,不知其果美。”(梁章巨《浪迹三谈》)中州(今河南)一段的黄河鲤鱼,在当时堪称“顶级美味”。
它执掌牛耳之际,长江流域的武昌鱼,尚且默默无闻,或根本上不了台面。古人“宁饮建邺水,不食武昌鱼”。直到当代,毛泽东写诗:“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武昌鱼的身价才大大提高,今非昔比。
我以为黄河鲤鱼与武昌鱼,可分别作为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吉祥物。
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人春节时供奉的千年之有“鱼”,不见得非用鲤鱼不可?我猜测是唐朝。因唐朝皇帝李姓,与“鲤”谐音,而举国禁止捕食鲤鱼。
老百姓置办年夜饭,当然也必须用别的鱼类代替。否则是违法的,要吃官司的。鲤鱼在唐朝,地位最高,真正跳进了人间的“龙门”,皇帝共命运,喻示着大唐之宏伟气象。
《大业杂记》:“清泠水南有横渎,东南至砀山县,西北八通济渠忽有大鱼,似鲤有角,从清泠水入通济渠,亦唐兴之兆。”后来,唐玄宗游漳河,亦曾见赤鲤腾跃,“灵皇之瑞也”。他老人家一高兴,就给鲤封了个爵位:“赤公”,并且下令写进“宪法”里。
鲤仿佛成了唐朝李姓皇帝的“远房亲戚”,不仅无人敢虐待,在世俗中的知名度乃至荣耀,似乎列于将相之上。
直到李唐政权垮台后,鲤才重新成为食物,端上百姓的餐桌。
鲤,做皇亲国戚的感觉,很好吧?
鲤,是否至今仍想“梦回唐朝”?
在中国,鲤的命运,本身就像一小部额外的“史书”。通过它,甚至可以“解构”历史,“解构”中国的图腾。
它不仅是一条古典主义的鱼、浪漫主义的鱼,更是一条现实主义的鱼,乃至象征主义(后现代?)的鱼。它自始至终都游泳在隐喻之中。光与影,形而下与形而上,共同制造了鲤的幻象,制造了鲤的喜怒哀乐。虽然它,作为实体,却浑然不觉,逗留于江山与水草之间,根本不知晓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导演”是谁。
中国人的想像力,赋予了鲤以更多的背景、更多的情节、更多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