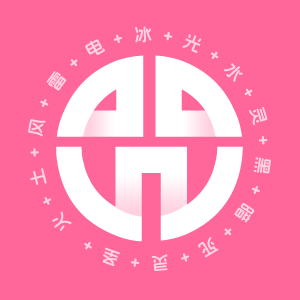网络文学的使命与当代文学的扩容
网络文学是当代文化景观中不可回避的一道风景,一方面释放出了巨大的文化产能,使得互联网产业在文化领域中发挥了重要的效能;另一方面,也使得网络作家和众多的文学写手获得了职业上的归属。作为一个新型的和已经发展起来的行业,网络文学已经得到了国家制度层面的认可。这体现了国家文化发展的包容度,也体现了国家制度层面上对网络文学的高度意识形态化。
然而,有评论家排出了文学的座次,网络文学似乎真的找不到自己的座次。这下问题来了,网络文学就像是一个凭空问世的家伙,戴着文字狰狞的面具,携着资本的基因,俨然成了一个游荡在互联网上的幽灵……
事实果真如此吗?答案是否定的。笔者从以下四组关系来看网络文学的“当代使命”及其历史境遇。
首先,我们需要对当代文学生态进行细部的考察。早期有影响力的网络文学几乎都是有悖于主流话语模式的新型叙述方式。在我看来,这是继“后先锋文学”之后的一种创造,这其中暗合了二十世纪末期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思想思潮。这些作品发表在互联网上,规避了传统期刊惯性的审稿制度,因此主要在互联网上传播。这个时期的作品并没有人将其命名为“网络文学”。
随后的一系列官方举措将网络文学彻底从“草根”文学上升到国家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2003年,起点中文网开始实施付费模式之后,大规模的网络发表成为一种现实,同时也吸引了无数的文学青年开始以网络创作作为一种谋生手段。自此,资本的参与加速了网络文学的生产和消费。2008年10月至2009年06月,在中国作家协会的指导下,《长篇小说选刊》联合中文在线旗下的17K网站联合承办“网络文学十年点评活动”(简称“网络文学十年盘点”)。这是中国网络文学重要的时间节点,也是网络文学第一次进入传统文学界的视野,也可以理解为,这是网络文学正式进入中国当代文学阵营的一次集体亮相。
其中十佳优秀作品为《此间的少年》《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新宋》《窃明》《韦帅望的江湖》《尘缘》《家园》《紫川》《无家》《脸谱》;十佳人气作品为《尘缘》《紫川》《韦帅望的江湖》《亵渎》《都市妖奇谈》《回到明朝当王爷》《家园》《巫颂》《悟空传》《高手寂寞》。这些作品如今大多数已经改编成影视作品。自此,“网络文学”从“草根”到身份完全被中国作协接纳。网络文学实现了在文学史意义上的耀眼呈现。
2013年下半年开始,中国作协经中宣部批准成立“全国重点文学园地联系会议”制度,对全国重点文学网站创作进行行业指导与扶持。时隔一年,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发表文艺座谈会讲话,其中指出“网络作家、签约作家、自由撰稿人、独立制片人、独立演员歌手、自由美术工作者”将是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有生力量。2015年9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其中特别提出“大力发展网络文艺”。许多行业内人士大呼网络文艺终于获得“正名”,预示着网络文艺的春天到来。
从传统文学史角度上来说,这样的时间节点已经与民间意义上的行业变革大不一致。人们通常会把1998年痞子蔡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作为网络文学的发生元年,2003年起点中文网付费模式作为第二次节点,而2015年的IP爆发作为第三个节点。相较于官方的规范裁定谱系来看,行业变革只可以看作是一种参考,或者是行业发展的视角而不是文学史意义上的网络文学发展谱系。
其次,关于网络文学的资本原罪与文学的关系。批评者认为资本寡头控制着网络文学话语权,简单地将网络文学与大网站划等号,在大网站与小网站,甚至除小说之外的其他体裁的文学网站之间划出是与非的界限。其实,这也是一种误判。网络文学也是百花齐放,并不能因为花香花大就无视其他花草的存在。客观上说,资本在网络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与国有文化企业一样,任何经营行为无资本是不现实的,不能因为民营资本涉足这个行业,就将网络文学套上资本逐利的标签进行一番道德批判。网络文学的主体不是资本而是“人”,资本是为“人”服务的,因此,只有对作者进行整体考察,才抓住了问题的主要矛盾。
目前,网络作者已经出现了分化趋势,从单纯的签约网站转让签约版权之外,不少有了名气的网络作者自己创业做公司,或者合伙做公司,在此基础上吸引资本合投娱乐产业,这也是未来的一个趋势。也就是说,网络文学版权所有人自主创业将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2007年1月由博易创为(北京)数字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主导的“望古神话”发布,由流浪的蛤蟆任首席架构师,月关、马伯庸、跳舞、天使奥斯卡五位作家创作的五部作品共同铺垫了其开端(月关作品《秦墟》,马伯庸作品《白蛇疾闻录》,流浪的蛤蟆作品《蜀山异闻录》,跳舞作品《选天录》,天使奥斯卡作品《星坟》)。目前,前三位作家的作品均已在天地中文网上线连载,《秦墟》和《白蛇疾闻录》已同步启动影视改编。
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可喜的转变:一是资本与作者的关系不再是单向的雇佣关系,而是混合的合股关系;二是内容上网络作家进入到另一种宏大的历史、文化叙事,如果简单地认为网络作家都是“目不识丁”的莽汉,似乎陷入“掩耳盗铃”的自戕。这是网络文学发生的新现象,势必出现新的格局。
再次,是文学功能的变异与超越。传统文学在本质属性上强调审美、教育等核心功能。归纳起来,传统文学的本质在童庆炳看来主要有“三义”,亦即文化的文学观念,审美的文学观念和惯例的文学观念[1]。在童先生看来,这种除了广义文学与狭义文学之外的折中义和惯例文学就指的是某种新文体、边缘文体或实验文体[2]。在我看来按照传统文学观念,网络文学当属童先生所认定的第三种文学即惯例文学观念。在传统文学观念那里,文学在本质属性上一般都认定“审美的意识形态”是作为本质属性的,因此派生出来的功能也是网络文学所不具备的。
网络文学属性里的文学性、类型化在传统文学中都不是抽象存在的,而这也不是网络文学区别传统文学的要义。要义是由传播技术和社交软件主导下的“对话性”和“社交性”,这才是网络文学区别传统文学属性和功能的核心所在。由此派生出网络文学的系列功能也就完全将“审美的意识形态”边缘化,甚至彻底消解化。这是网络文学的真正原罪,而不是资本原罪说[3]。
四是网络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关系。客观上说,网络文学积聚着大量的人气,特别是资本的推波助澜,使得网络文学成为网络文艺的主要样式,客观上遮蔽了其他体裁的文学网站和文化网站。根本上说,这不是网络文学本身的问题。既然作为主要样式,是否可以将网络文学排斥在文学之外?我想,这里需要厘清一个核心的问题,也就是“什么是当代文学”。如果没有这个前提,简单地否定网络文学对于当代文学的意义或者干脆得出“网络文学就是网络文学”的结论,似乎显得武断,也落入到机械唯物主义的窠臼。关于这个核心问题,笔者有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关于“当代”,陈晓明认为,“何为当代?体现了一体化和规范化的形成建立过程,这就是‘当代’。换句话说,当代性就存在于这样的历史过程中,是其内在性的质。然而,到了80年代,‘当代’走向了其反面,在变革、转折、解构的过程中,‘当代’的本性才体现出来,或者说才实现了‘当代性’。在这一意义上,‘当代性’既是先验的,又是被建构起来的”[4]。那么,我们现在所论及的“当代性”恰恰可以在网络文学上得到体现,传统文学对于社会思潮的反应几乎是无效的,而传统文学期刊几乎又被主流作家和艺术家所垄断。网络作者的现实处境本身就是中国现实的一个缩影,看网络作者的生存状态就是看当代本身,这比文学还要文学。因此,“人”才是“当代性”的核心之一。
笔者曾在“首届中国网络文学论坛”上发表《新穷人是网络文学的最大市场》的主题演讲[5]。恰恰相反的是,并不是网络作家“草根”返正后的道德优越,而是偏见与傲慢忽视了最大的文化民间性。网络文学积聚着庞大的人群,同时,最具活力的作者团体也有孕育若干“先锋”的可能性,这是建构网络文学的现实价值立场的实践基础,当代文学没有必要回避这样的现实。因此,国家对网络文学的重视,客观上也是对基层民众人权的尊重,体现出网络文学本身所蕴含的伦理价值。
第二,网络文学与平民化,中国网络文学与欧洲“艺术平民化”运动有着本质的不同。欧洲19世纪末的时候,出现了一股“艺术平民化”思潮,但是艺术家与“人民”并没有能沟通起来,按照盖格尔的说法是,“这样的人民充其量只能恭敬地观看它们,不过,与这些东西相比,他们更喜欢观看那些刊有富有魅力的女郎的杂志画面,甜蜜怡人的广告招贴画,更喜欢倾听那些流行歌曲”[6]。到了“艺术平民化”第二阶段,是随着批量生产的技术的发展开始的,“艺术并没有把广大公众吸引到它身边来,而是广大公众把艺术降低到了他们所处的水平上了;艺术是一种追求享受的手段,这种概念是唯一可能得出的结论”[7]。网络文学来源于民间,开启了大众写作的热潮。也在改变着当代文学创作的版图。特别是网络文学潜在的“对话性”既是区别传统文学的根本所在,也是网络文学成为新经济形态的主要引擎,“特别是互联网平台的在线性和及时性使得这样的对话更为便捷和真实。如果说传统文学中的‘对话关系’是带有系统性的逻辑思维特征,而网络文学则更为直观、直接和纯粹。这是传统文学所不具备的。这也是网络文学成为粉丝经济、眼球经济的最为主要的推手之一”[8]。
第三,当代文学碎片还是网络文学碎片?批评者认为网络文学质量不高,无法被当代文学吸纳,我觉得这是个伪命题。从整体性而言,文学是整个一个时期内的文化观照者,既有意识形态的具体干预,同时又有自身的独立审美的存在。网络文学固然存在事实价值领先审美价值的现实,甚至事实价值取代审美价值,但这不是考量网络文学能不能被当代文学接纳的核心。也就是所谓的“享受”让位于“快乐”原则,就据此作为不该被接纳的证明。在我看来,网络文学具有较强的吸收与矫正功能,它正在与传统文学形成互融,这是当代文学发生的新的现象,不应该忽视这种互融共生的现实。
第四,随着网络文学逐渐被学院化,这将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必将开启网络文学新的创作形态与新的创作方式。在尊重基本艺术规律的同时,一方面遵循网络文学的发展规律,另一方面对网络文学内容生产进行必要的训练与引导。同时,鲁迅文学院和各省作家协会等机构大面积的网络文学作者培训也是一种补充。新的文化业态在新制度的催生之下不断完善自身的成长机制,共同促使网络文学得到不断的优化,“它的任务是,通过外在的专注来发现那些存在于音乐、文学,以及存在于各种视觉艺术之中的价值,引导人们离开赤裸裸的享受,去追求那可以享受的欣赏”
[9]。因为,止步于“爽点”不是网络文学的最终归属。
诚如陈晓明所说:很显然,当今中国文学不只是表现出中国民族的生存境遇,文学也以它自身的矛盾性显现出一种文化的历史境遇。尤其是文学,它以语言形式传承的传统性,它经受着的世界文学的挑战,它承受着当下汇集的矛盾和压力,中国文学在今天何去何从,它想怎么做,它能做什么——所有这些,都表明了它处于一种历史境遇中,它只有意识到这个境遇,深刻领悟了现实的命运和未来的召唤,才能走出自己的道路。道路从境遇中生长,在当下艰难开掘,向未来坚韧延展,中国文学因此才有力量,才能超越“当代性”
[10]。网络文学需要学界的包容与正视,这既是一种学术上的关怀,也是对中国民间文学实践的一种尊重。
毋庸危言,网络文学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但这样的问题仍旧在文学自身,业界对此也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一方面虚心接受来自文学内部的批评,同时,也在接受社会的监督,特别是对于有建树意识的作者而言,他们有着极高的道德荣誉感,也有自我修复的迫切愿望。这是网络文学走向自觉的一个新阶段。任何对网络文学文本低劣的指责或是对其前途的唱衰和焦虑,都是对网络文学的误读,甚至就是误解和棒杀。
(本文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网络文艺委员会委员)
注释:
[1][2]
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4月第二版,第50、53、59页。
[3][8]
吴长青:《网络文学研究中的几个关键词》,《网络文学评论》2017年第1期。
[4][10]
陈晓明:《论文学的“当代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6期。
[5]
吴长青:《新穷人是网络文学的最大市场》,搜狐文化:
http://mt.sohu.com/20151013/n423096456.shtml
[6][7][9]莫里茨·盖格尔:《艺术的意味》,译林出版社,2012年1月版,第119、1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