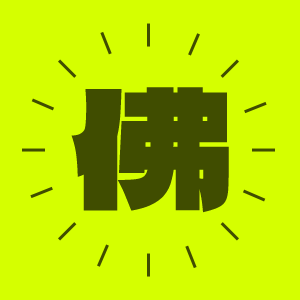蒋胜男: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为什么是辽?为什么是萧燕燕?这大概是每一个打开《燕云台》的读者对我所创作的故事背景、以及选人角度的最初疑惑。
我们过去比较多习惯于这样的历史书写:以大一统王朝作为背景下的皇权争斗、清官反腐、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权力博奕,官场的明争暗斗。这个类型出了许多精品,但同时也容易形成写作历史小说的模式化。作为亲身经历改革开放的一代人,作为在网络生态下地球村概念的一代人,我想比起大一统时代之下权力内卷化的历史小说我们已经看得太多,我们向书中寻找的,其实是时代的困惑。过去“非黑既白”的意识形态历史表述方式在新的时代前,是否还可以有另一种表述方式?
我们能否向历史去叩问,我们的前人在面临同样的问题时,是怎么处理的。我们是否想看到另一种类型的历史小说,是否想知道在某个“大变局”面前,身处其中的人会怎么想,在他当时的环境中,会怎么选择。
当人类站在历史和命运的十字路口,其实并没有绝对的政治正确就能成功,恰恰相反,很可能是那个时代最聪明的人都不知道自己的选择到底是对还是错。而研读者能提供的,就是给这个世界更多的案例和解读方式,可以提供下一个十字路口的人们,能够有更多案例可选择。
而我们是怎么找到这个思维模式,怎么样在不同的文化思维传统下互相理解,去寻找属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解读?
尤其是《芈月传》以后,这个想法强烈了。惯常的创作思路,通常会因为秦一统天下,而只愿意陈述秦的绝对正确。但法家文化的确助秦一统天下,可是汉朝前期推行的是道家的黄老之术,这是出自楚国,而后来的儒家又是出自齐鲁。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百家的文化都是属于中华民族的丰厚遗产。我们应该从前人的智慧中去学习,在地球村这个时代重要的不是在冲突、对立中谁取得暂时的胜利,而是谁能够在多元文化中取得共融共存。
在《芈月传》之前,我就有对于宋辽夏创作的设想。原本只是打算从北宋一个点切入来写,然而随着资料挖掘的不断深入,创作越来越渲染于其中的时候,我发现对于这个时代而言,仅仅只有一个故事是不够的,对于历史的触摸,不仅仅只是一时一地一区域思维的限定,而应该站在大历史大视野的格局去重新看待那个时代的风起云涌。
我想,我们不止是用宋的眼光看辽和夏,还应该用辽的眼光看宋和夏、用夏的眼光看宋和辽。换了一种视角去看历史,也更能去理解当时这些历史人物为什么会去做那样的抉择。
历史长河中每一个留下来的人物都构成了历史的一部分。而澶渊之盟是一个划时代的标记。当时的宋辽统治者考虑到唐末以来100多年的战乱,克制住了自己的政治欲望,120年的和平带来了宋的文化繁荣昌盛和辽的发展,也为后世提供了解决修昔底德陷阱的答案。
对于我来说,故事是一条船,我更希望我的读者因故事而来后,看到的能是属于那个时代的长河。正如我写《芈月传》之前,我想写的并不是个人,而是想写那个春秋战国的时代。因为有了这些个体的爱恨情仇的故事,才能让更多的读者愿意去耐下心来,去关心那个离我们现在很遥远的时代。
这艘船,可以是一位女性,当然也可以是男性。比起后天赋予的性别壁垒,我更在意的是,这个时代哪一个个体来代表更合适?谁能够承载起航行的责任,将读者带到历史的镜面前?
我选择萧燕燕成了这个落点,承载起了那个时代转折变迁的最大故事量,成为那一艘将浩瀚的历史长河引渡到人们眼前的小船。但同时,历史的镜像不会只有她一个人的悲欢,萧燕燕的亲人和爱人,萧燕燕一生路过的君王、朝臣,甚至仅仅是惊鸿一瞥的某个小配角,他们不是彼此的敌人,而是彼此的镜子,折射当时在民族融合的十字路口,不同身份、位置的人面临的选择和他们背后的得意或失落。
从《芈月传》到《燕云台》,对我自己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在头10万字写完时,我自己回头看很不满意,因为整体的文风还停留在《诗经》《楚辞》《战国策》的典雅中。于是我放下电脑,来到赤峰,站在大草原上,站在辽上京遗址上感受着草原民族粗犷直白的感觉,我找到了感觉,把之前的10万字放弃,然后重新开始。
而这种改变,开始甚至会被误读,会被喜欢我作品的亲友读者质疑文笔是否退步了,是否失去了我曾在《芈月传》中的那种文质彬彬、典雅优美?而恰恰在这时,我才松了一口气,这种质疑恰恰说明我的创作路子对了。创作要从故事本体出发,让写先秦的故事有先秦感,而写辽国的故事有草原感。如果只求“文笔”或者“典故”就纯只是一种炫技。而小说写作中,不符合创作意图,没有必要的炫技就是浪费和臃肿。
对萧燕燕描写是一种新的类型,她不同于我以往创作中的人物,是自带着极强大的压力,而对于创作者来说,压力越大,反弹越大,越有戏剧性。但萧燕燕不同,如果从历史材料来看,至少在她入宫以前的经历来说,她出身高、环境顺,就很难给她自身安排太大波折。所以我改变思路,从祥古山开始,先制造整体政治大情境和朝堂上的风云变化,来为萧燕燕安排情节,不去故意设置戏剧性的压弹簧,而是宁可从史料和情理出发的“顺着来”,虽然这对自己的创作提出了新的挑战,但同样更能够找到因此而带来的兴奋感。
对于历史人物的创作来说,如果全部按照历史记载去创作,这就失去了小说的趣味性,如果天马行空地全靠自己杜撰,这就是胡编乱造。所以我当时在创作的时候,更希望是在不动大历史的框架下,去填充这些人物之间的情感细节。而我想的是把能找到的历史资料都找出来先放置好,就像一个法医把能拿到的骨头碎片和毛发都先放到一起,然后用自己的“DNA系统”也就是自己大量阅读海量历史材料所构建的体系,去拼凑出骨架,再慢慢长出肌肉,用DNA去还原这个人物。让每一个人物都是用自己的性格去决定自己的命运。再从这些人物的选择当中倒推出历史进程中事件的可能模样。
当萧家的三个姐妹分别嫁给了皇族三支,故事就会逐渐走向高潮。耶律阿保机留下的三支都有机会争夺皇位,而三个姐妹都有能力辅佐自己的丈夫。当这些从小就站在高处的女孩子卷入政治漩涡的时候,很难不被权力影响。不管她曾经有没有说过自己对权力的渴望,这份心思其实早就已经植根在她们的脑海里。这种原始的权力驱使,会让这三个姐妹朝着自己的性格和欲望而去。当我们赋予人物性格原动力,她们就会替我们作出应有的选择。所以故事写到最后,我自己也很感慨。每一份选择、每一份割舍都是基于人性的选择,而非“作者之手”。
写作是一件苦事,也是一件乐事。研究一件事情,想明白它,再演绎出来,通过纵横的五千年,作者的内心也在不断地被扩展。这个学习新知和“破壁”的过程中,最重要的甚至不是创作出一个怎样的故事,而是创作中带来的对自我思想的冲击与洗涤。在我多年的写作生涯里,创作过大量的戏曲、武侠、玄幻、言情等题材的小说,我认为它们都是有意义的,是在为我写历史小说练笔,帮助我更好地驾驭历史题材的创作。即便是现在,我依然觉得在浩瀚的历史面前,个人原有的视野和想象是相当局限和狭隘的。
我们常说“以史为鉴”,历史其实就像一面镜子,能够照出人类曾经所有的困惑、痛苦。这些情感是共通的,是能够超越历史、映照当下的。